|жқңдё№ | е…ұз”ҹгҖҒиҪ¬иҜ‘дёҺдәӨдә’пјҡжҺўзҙўеӘ’д»Ӣзү©зҡ„дёӯд»ӢеҢ–
жң¬ж–ҮжҸ’еӣҫ
жң¬ж–ҮжҸ’еӣҫ
дҪңиҖ…пёұжқңдё№
ж‘ҳ иҰҒ
еңЁеӘ’д»Ӣзү©иҙЁжҖ§и¶ҠжқҘи¶Ҡеј•иө·дј ж’ӯеӯҰз ”з©¶йҮҚи§Ҷзҡ„жғ…еҶөдёӢ пјҢ еӘ’д»Ӣзү©зҡ„дёӯд»ӢеҢ–й—®йўҳиҝҳжңӘеҫ—еҲ°е……еҲҶжҺўи®Ё гҖӮ жң¬ж–Үе°ҶвҖңиә«дҪ“-еӘ’д»Ӣзү©вҖқе…ұз”ҹдҪ“дҪңдёәз ”з©¶иө·зӮ№ пјҢ йҖҡиҝҮжўізҗҶжӢүеӣҫе°”зҡ„жҠҖжңҜе“ІеӯҰе’Ңе”җВ·дјҠеҫ·зҡ„еҗҺзҺ°иұЎеӯҰдёӯе…ідәҺвҖңдәәдёҺжҠҖжңҜзү©зҡ„дёӯд»ӢеҢ–е…ізі»вҖқзҡ„жҖқжғі пјҢ жҸӯзӨәпјҡе…·иә«дәҺиә«дҪ“зҡ„еӘ’д»Ӣзү©е…·жңүе·®ејӮжҖ§зҡ„дёӯд»ӢеҢ–ж„Ҹеӣҫ пјҢ жҳҫзҺ°еҮәвҖңдёҠжүӢвҖқдё”вҖңйҖҸжҳҺвҖқзҡ„е…ұеҗҢж„Ҹеҗ‘пјӣе®ғ们еңЁдёҺиә«дҪ“зҡ„иһҚеҗҲдёҺдәӨдә’дёӯжҖ»жҳҜиҪ¬еҸҳдәәзҡ„иЎҢеҠЁдё”и°ғиҠӮдәәзҡ„дҪ“йӘҢпјӣеӘ’д»Ӣзү©дёӯд»ӢдәҶдәәдёҺзү©гҖҒзү©дёҺзү©д»ҘеҸҠдәәдёҺдәәд№Ӣй—ҙзҡ„дҝЎжҒҜдј йҖ’дёҺжІҹйҖҡдәӨеҫҖ пјҢ жү“йҖ еҮәж—Ҙеёёз”ҹжҙ»зҡ„зү©иҙЁжҖ§вҖңиҒ”зӣҹвҖқ гҖӮ иҝҷдёҖиҒ”зӣҹжҳ“еҪўжҲҗвҖңеӘ’д»ӢеҢ–вҖқзӨҫдјҡдёӯзү№е®ҡ科жҠҖгҖҒж–ҮеҢ–гҖҒе•ҶдёҡдёҺж„ҸиҜҶеҪўжҖҒзҡ„еһ„ж–ӯ пјҢ е°Ҷдәәи®ўйҖ гҖҒдҝғйҖјдё”зү©еҢ– пјҢ д»ҺиҖҢдә§з”ҹж–°зҡ„дәәдёҺжҠҖжңҜзҡ„еҶІзӘҒдёҺиҫғйҮҸ гҖӮ
е…і й”® иҜҚ
еӘ’д»Ӣзү©; дёӯд»ӢеҢ–; иЎҢеҠЁ; зҹҘи§ү; дәӨдә’
1еј•иЁҖ
еңЁж—Ҙеёёз”ҹжҙ»дёӯ пјҢ жҲ‘们з©ҝиЎЈгҖҒејҖиҪҰгҖҒжҲҙзңјй•ңзӯү пјҢ ж— дёҚдҪ“зҺ°еҮәиә«дҪ“дёҺжҠҖжңҜзү©зҡ„зӣёдјҙзӣёз”ҹ гҖӮ дәәйҖҡиҝҮжҠҖжңҜзү©еұ•ејҖзҡ„е…·иә«еҢ–пјҲembodyingпјүе®һи·өдёҚд»…е°ҶпјҲеҜ№иұЎеҢ–зҡ„пјүжҠҖжңҜзү©иҪ¬еҸҳдёәеӘ’д»Ӣ пјҢ иҖҢдё”дәәзҡ„з»ҸйӘҢиҝҳеҸҜиғҪжҝҖжҙ»жҲ‘们жүҖзҶҹзҹҘзҡ„еҗ„з§ҚеӘ’д»Ӣе®һи·өзҡ„зҺ°иұЎгҖҒд№ жғҜе’ҢзҹҘиҜҶ пјҢ её®еҠ©жҲ‘们жҖқиҖғеҗ„з§ҚеӘ’д»Ӣзү©дёҺдәәзҡ„е…·иә«е…ізі» пјҢ д»ҺиҖҢеҜ№ж–°жҠҖжңҜзҺҜеўғдёӢдәәзҡ„з”ҹеӯҳзҠ¶жҖҒгҖҒдәӨеҫҖж–№ејҸ пјҢ д»ҘеҸҠдёӯд»ӢеҢ–зҡ„зҺ°е®һеұ•ејҖжҺўзҙў гҖӮ
дәәйҖҡиҝҮеҗ„з§ҚпјҲ移еҠЁпјүжҷәиғҪз»Ҳз«ҜгҖҒдә’иҒ”зҪ‘дёҺдәәе·ҘжҷәиғҪжҠҖжңҜпјҲ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пјүеұ•ејҖе…·иә«еҢ–зҡ„дј ж’ӯе®һи·ө пјҢ е°ұжё…жҷ°ең°дҪ“зҺ°дәҶдёҠиҝ°жҖқз»ҙеҸ–еҗ‘ гҖӮ жҜ”еҰӮ пјҢ дәәйҖҡиҝҮжүӢжҢҒжҲ–з©ҝжҲҙжҷәиғҪз»Ҳз«ҜжҺҘе…Ҙдә’иҒ”зҪ‘ пјҢ еұ•ејҖеҠЁжҖҒзҡ„зӨҫдјҡз”ҹжҙ»дёҺдәәйҷ…дәӨеҫҖпјӣи„‘жңәжҺҘеҸЈжҠҖжңҜ[1]её®еҠ©жҠҖжңҜе…·иә«[2]зҡ„ж®Ӣз–ҫдәәиЁҖиҜҙдёҺиЎҢеҠЁпјӣеҹҺеёӮз©әй—ҙдёӯж— еӨ„дёҚеңЁзҡ„ж— зәҝзҪ‘з»ңпјҲWi-FiпјүжӯЈи¶ҠжқҘи¶Ҡжҷ®йҒҚең°еҚ·е…Ҙдәәзҡ„е…·иә«еҢ–е®һи·өпјӣдәәйҖҡиҝҮдј ж„ҹеҷЁгҖҒиҠҜзүҮе’Ңдә‘е№іеҸ°зӯү пјҢ е®һзҺ°вҖңзү©вҖқдёҺвҖңзү©вҖқд№Ӣй—ҙзҡ„дҝЎжҒҜиҒ”йҖҡвҖҰвҖҰжӯЈеҰӮе…ӢеҠіж–Ҝ·延森пјҲKlaus JensenпјүжүҖиҜҙ пјҢ ж•°еӯ—еӘ’д»Ӣзҡ„вҖңжҷ®йҖӮи®Ўз®—вҖқпјҲUbiquitous Computingпјүе·Іе°ҶвҖңдҝЎжҒҜеӨ„зҗҶиҝҮзЁӢдёҺж—Ҙеёёзү©д»¶жҲ–ж—Ҙеёёжҙ»еҠЁиһҚдёәдёҖдҪ“вҖқпјҲ延森 пјҢ 2010/2012:86пјү пјҢ е®һзҺ°дәҶдәәдёҺи®Ўз®—жңәгҖҒпјҲ移еҠЁпјүжҷәиғҪз»Ҳз«ҜгҖҒзі»з»ҹе’Ңеә”з”ЁзЁӢеәҸзӯүеӘ’д»Ӣзҡ„иһҚеҗҲпјҲfusionпјүдёҺиҒ”зҪ‘е·ҘдҪң гҖӮ дёҠиҝ°дј ж’ӯзҺ°иұЎжӯЈй©ұеҠЁзқҖеӯҰиҖ…们еҜ№еҗ„з§ҚжіӣеңЁзҡ„еӘ’д»Ӣзү©гҖҒдәәдёҺеӘ’д»Ӣзү©зҡ„е…·иә«е…ізі»еұ•ејҖзҗҶи®әжҺўзҙўдёҺеҸҚжҖқ гҖӮ
еңЁдё»жөҒдј ж’ӯеӯҰзҡ„и§ҶйҮҺдёӯ пјҢ еӘ’д»Ӣз ”з©¶йҮҚи§ҶеӨ§дј—еӘ’д»ӢжүҝиҪҪзҡ„ж–Үжң¬еҶ…е®№дёҺж•Ҳжһң пјҢ иҖҢзӣёеҜ№еҝҪз•Ҙиә«дҪ“дёҺеӘ’д»Ӣзҡ„зү©иҙЁжҖ§ пјҢ ејәи°ғдј ж’ӯжҳҜвҖңзІҫзҘһдәӨеҫҖеҸҠдә’еҠЁвҖқ пјҢ жҳҜйқһзү©иҙЁжҖ§зҡ„жҙ»еҠЁ пјҢ еӘ’д»ӢжҳҜеҜ№иұЎеҢ–зҡ„е·Ҙе…· пјҢ жҳҜвҖңзӨҫдјҡеҝғзҗҶе®һи·өвҖқвҖңж–Үжң¬е®һи·өвҖқе’ҢвҖңжңәжһ„е®һи·өвҖқеұӮйқўдёҠзҡ„еӘ’д»ӢпјҲе”җеЈ«е“І пјҢ 2014пјү пјҢ еҸҲжҲ–жҳҜдҪңдёәвҖңиҜқиҜӯвҖқдёҺвҖңеҲ¶еәҰвҖқзҡ„еӘ’д»ӢпјҲ延森 пјҢ 2010/2012:61пјүпјӣеӘ’д»ӢзҗҶи®әдёҺдј ж’ӯз”ҹжҖҒеӯҰд№ҹе°ҶеӘ’д»ӢжҠҖжңҜи§Ҷдёәдј ж’ӯзҡ„жүӢж®өгҖҒе·Ҙе…·е’Ңе№іеҸ° пјҢ и®ӨдёәеӘ’д»ӢжҠҖжңҜй©ұеҠЁзӨҫдјҡе’Ңж–ҮеҢ–еҸҳиҝҒ гҖӮ иҝҷдәӣз ”з©¶ејәи°ғеӘ’д»Ӣзҡ„зӨҫдјҡеұһжҖ§ пјҢ жҳҫзӨәеҮәвҖңеҚ•дёҖзҡ„еҹәдәҺеӘ’дҪ“зҡ„йҖ»иҫ‘вҖқпјҲжҪҳеҝ е…ҡ пјҢ 2014пјү пјҢ еҝҪи§ҶдәҶдёҖиҲ¬ж„Ҹд№үдёҠдәӨеҫҖиҝҮзЁӢдёӯеӘ’д»Ӣзү©зҡ„дёӯд»ӢеҢ–дҪңз”Ё пјҢ ж•…иҖҢж— жі•жӣҙж·ұе…Ҙең°зҗҶи§ЈгҖҒжҸҸиҝ°е’Ңи§ЈйҮҠдәәйҖҡиҝҮеӘ’д»Ӣзү©еұ•ејҖзҡ„ж—ҘеёёдәӨеҫҖе®һи·ө пјҢ 并еӣһеә”зӨҫдјҡжҳҜвҖңеӣҙз»•зқҖе…ұжңүзҡ„е®һи·өзҗҶи§ЈиҖҢиў«йӣҶдёӯз»„з»Үиө·жқҘзҡ„дёҖдёӘе…·иә«еҢ–зҡ„дёҺзү©иҙЁдәӨз»ҮеңЁдёҖиө·зҡ„е®һи·өйўҶеҹҹвҖқпјҲеӨҸе…№йҮ‘ пјҢ еЎһи’Ӯзәі пјҢ иҗЁз»ҙе°ј пјҢ 2000/2010:10пјү гҖӮ
иҝ‘е№ҙжқҘ пјҢ йҡҸзқҖдёҠиҝ°еӘ’д»ӢжҠҖжңҜзҡ„еҸ‘еұ•дёҺжҷ®еҸҠ пјҢ дёҖдәӣеӯҰиҖ…е·Із»ҸйҮҚи§Ҷдј ж’ӯдёӯзҡ„иә«дҪ“дёҺеӘ’д»Ӣзү©иҙЁжҖ§зҡ„й—®йўҳ гҖӮ еҲҳжө·йҫҷпјҲ2018,2019пјүи®ӨдёәвҖңиә«дҪ“еә”иҜҘйҮҚеӣһдј ж’ӯвҖқ пјҢ е…·иә«жҖ§дёәе…із…§ж–°дј еӘ’жҠҖжңҜе®һи·өжҸҗдҫӣдәҶйҡҫеҫ—зҡ„йҖ»иҫ‘еҲҮе…ҘзӮ№ гҖӮ ж јйӣ·еҺ„е§ҶВ·й»ҳеӨҡе…ӢпјҲMurdock,2019пјүи®ӨдёәеӘ’д»Ӣзү©иҙЁжҖ§жӯЈеңЁд»ҺеӘ’д»Ӣз ”з©¶зҡ„зӣІзӮ№иҪ¬еҸҳдёәдёӯеҝғпјӣз« жҲҲжө©дёҺеј зЈҠпјҲ2019пјүиҒҡз„ҰжӯЈеңЁеҸ‘з”ҹзҡ„вҖңеӘ’д»Ӣзү©иҙЁжҖ§иҪ¬еҗ‘вҖқ пјҢ жўізҗҶдәҶеҗ„з§Қзӣёе…ізҡ„зҗҶи®әжәҗжөҒе’ҢжҖқжғіжҙҫеҲ« гҖӮ е°ұиә«дҪ“дёҺеӘ’д»Ӣзү©зҡ„е…ізі»иҖҢиЁҖ пјҢ з« жҲҲжө©жҸҗеҮәвҖңзқ№зү©жҖқдәәвҖқ пјҢ еұ•жңӣвҖңеңЁзү©дёҺдәәзҡ„жҳ з…§дёӯеҸ‘зҺ°ж–°зҡ„е…ізі»вҖқ пјҢ еҲҳжө·йҫҷдёҺжқҹејҖиҚЈпјҲ2019пјүеҲҷи®ӨдёәвҖңзү©вҖқиҝһжҺҘиә«дҪ“ пјҢ жү®жј”зқҖдёӯд»Ӣзҡ„и§’иүІ пјҢ еҜ№ж•ҙдёӘзӨҫдјҡиө·еҲ°з»„з»Үе’ҢеЎ‘йҖ зҡ„дҪңз”Ё гҖӮ дёҠиҝ°з ”究жҲҗжһңдёҺи§ӮзӮ№зҡ„жўізҗҶжҸҗзӨәжҲ‘们 пјҢ е°Ҷиә«дҪ“дёҺеӘ’д»Ӣзү©и§ҶдёәдёҖдҪ“ пјҢ иҖғеҜҹдәәдёҺеӘ’д»Ӣзү©зҡ„е…·иә«е…ізі» пјҢ е°Ҷдҝ®жӯЈеӘ’д»Ӣзү©иҙЁжҖ§з ”究дёӯзҡ„дәҢе…ғеҜ№з«ӢжҖқз»ҙ пјҢ еҗҢж—¶ пјҢ е…·иә«е…ізі»дёӢзҡ„еӘ’д»Ӣзү©зҡ„дёӯд»ӢеҢ–жҲҗдёәжҲ‘们еҝ…йЎ»жҖқиҖғзҡ„й—®йўҳ гҖӮ
жҺЁиҚҗйҳ…иҜ»
- еҝ«з§‘жҠҖдәәжңәе…ұз”ҹпјҒ马ж–Ҝе…Ӣз§°и„‘жңәжҺҘеҸЈдёҖе№ҙеҶ…жӨҚе…Ҙдәәи„‘пјҡдҝ®еӨҚд»»дҪ•еӨ§и„‘й—®йўҳ
- гҖҢеҹғе°”жі•е“Ҙе“ҘгҖҚеңЁдёҡеҠЎдёӯдёҺAIе»әз«Ӣе…ұз”ҹе…ізі» дәәе·ҘжҷәиғҪдёәж•ҙдёӘд»·еҖјй“ҫеҲӣйҖ ж–°жңәдј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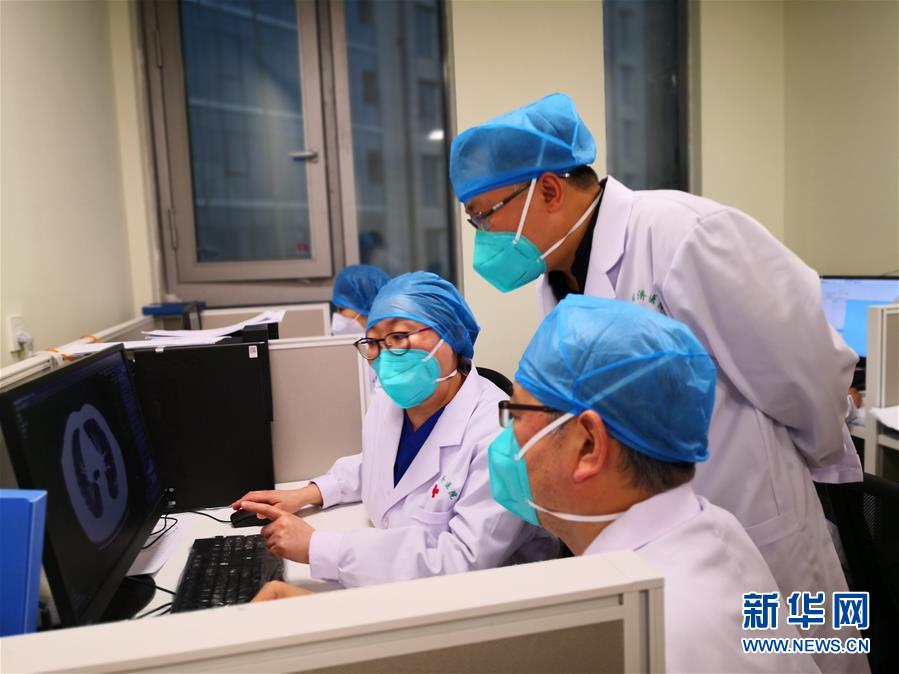









![[з”өжұ ]жңҖдјӨжүӢжңәзҡ„е……з”өж–№ејҸпјҢдёҘйҮҚеҪұе“Қз”өжұ еҜҝе‘ҪпјҢдҪ дёӯжӢӣдәҶеҗ—пјҹ](http://img88.010lm.com/img.php?https://image.uc.cn/s/wemedia/s/upload/2020/1fd9f2cf9a7f4fc1d5113622f942d2f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