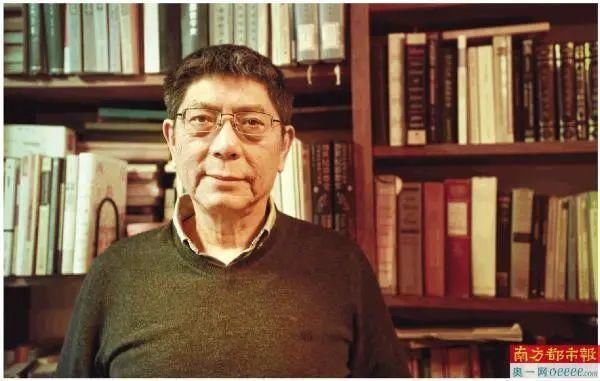
文章插图
陈嘉映近照王森 摄
陈嘉映,1952年生,先后任教北京大学哲学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著有《海德格尔哲学概论》《〈存在与时间〉读本》《无法还原的象》《从感觉开始》《旅行人信札》《哲学·科学·常识》《说理》《白鸥三十载》《价值的理由》《简明语言哲学》《何为良好生活》等;译有《存在与时间》《哲学研究》《哲学中的语言学》《感觉与可感物》《哲学与伦理学的限度》等。
本文转载于《南方都市报 》(2020年12月27日),作者为黄茜。
为给“南都2020年度十大好书”发布活动拍摄视频,我们去拜访了哲学教授陈嘉映。他居住的小区位于京西,环境清幽。冬日下午,阳光和暖地照在层层叠叠的书架和黑色钢琴上。家里有一双布偶猫,时常灵巧地在人脚边绕圈玩耍。
陈嘉映是一位宽厚长者,也是许多年轻人心中的学术偶像。他精研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在学术领域有丰富的创建。他的著作——尤其非学术专著类型——既思力深刻,洞烛幽微,又能阐发明晰,具体切己,很受读者大众的喜爱。今年,陈嘉映的新书《走出唯一真理观》获得“南都2020年度十大好书”殊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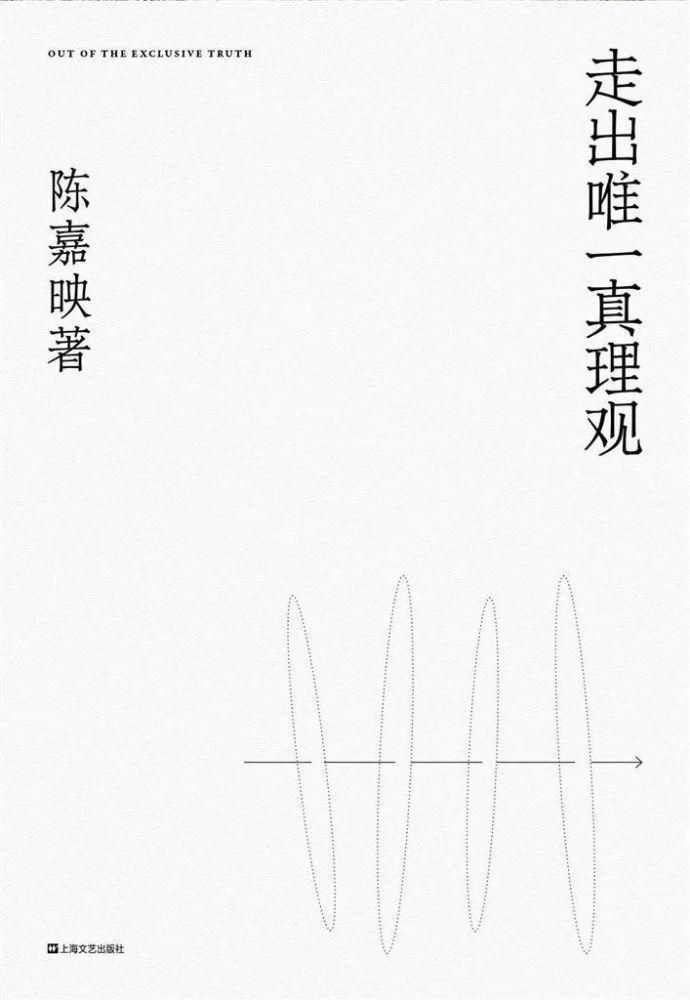
文章插图
陈嘉映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
这是一本以对谈、采访、演讲和书评为主体的集子,话题涉及艺术与现实、爱情与死亡、教育与洗脑、说理与对话、反思与过度反思、知识分子、人工智能等方方面面,谈话者学识渊博,譬喻精妙,常有令人会心一笑的类比和启人省思的洞见。尤其是与艺术家向京的对话《我们不再那样感受世界》,与刘擎、慈继伟、周濂的《“说理”四人谈》等,是杰出头脑之间的智识交锋,十分精彩。
相对而言,我们的访谈没有设定好的主题,大可称之为“漫谈”。如果一定要有一个潜在的“主题”,大约是当代人日益挥之不去的“焦虑感”。2020年,疫情来袭,科学暴露出意想不到的短板;与此同时,隔离挑战了人类心理底线,而移动互联网重塑了“共同生活”的方式;与此同时,行业内卷,打工人面临的生存竞争空前酷烈。在此境况下,阅读何为?思想者何为?
陈嘉映当然有自己的思考。他认为,这焦虑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我们过分安逸的生活,来自于“娇惯的心灵”——“时代娇惯我们,我们自己也在娇惯我们自己。”我们生活得安逸吗?辩证地看,安逸和酷烈,是当代生活的一体两面。而在陈嘉映眼里,所谓“良好生活”,只能从生存与劳作的直接性中获得。与其被情绪裹挟或在反思中漂浮,他更推崇那个“寻路阿富汗”的英国人罗瑞·斯图尔特——行走是为了“身体和灵魂得到锻炼、考验、折磨”,只是为了行走中所带来的一切,就像所有最有意义的事情,就像生活本身那样。
“我们是最后一代读书人”
南都:能不能讲讲您的个人阅读史?
陈嘉映:你要从小时候讲,就跟所有的孩子都一样。我最开始阅读的时候,爱读小说,主要读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类。之后读现代中国小说,五六十年代的长篇小说,什么《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之类,这些你们可能都不读了。到了中学,更爱读科学类书籍。然后就到了“文革”时期,那是一个比较大的转折,我不合潮流,读中国古典,唐诗宋词、司马迁、孔孟。再到后来,去插队,开始跟我哥哥读哲学。那个时候读书更系统,分门别类的,读历史、经济学,读科学,制定了计划读书,一门一门课自学。我们这代人,读书几乎是受教育的唯一方式,那时候也没有电视什么的。在我看,我们是最后一代读书人。以后只会有个别的人一味读书。
南都:现阶段您读书主要偏重哪些类型?
陈嘉映:多半时间用来读跟正在钻研的问题相关的,现在这段时间跟意识(consciousness)问题相关的读得比较多。谈到意识,你会扩展到身心关系,扩展到因果性(causality)什么的。此外的阅读我叫做闲读,或泛读,我个人兴趣比较大的一块儿是读历史,另一块儿是科普书,都是我持久的阅读兴趣。现在科学分得很细,进展又很快,像我这种没有受过系统科学教育的,想去真正钻研一门科学,既没这能力也没这精力,但感兴趣,就去读科普书。此外当然乱七八糟什么都读,只是读文学比年轻时候少了很多。
推荐阅读
- 如何直观地说明汉朝到底有多强大?
- 罗素:对平庸的崇拜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恶之一
- 深度阅读,慧眼识金,找到宝藏
- 把“穷”与“富”拆开看,原来如何致富古人早告诉我们了,千年无人知
- 经工集团党委开展革命传统教育
- 很快,我们的古典乐、民乐都将得到很好的传承和延续。“
- 成语故事:牛角挂书
- 诗鲸2068《每一个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
- 油画中的美人都跑了出来,就藏在我们周围,你能发现她们吗
- 一代儒将诗意雄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