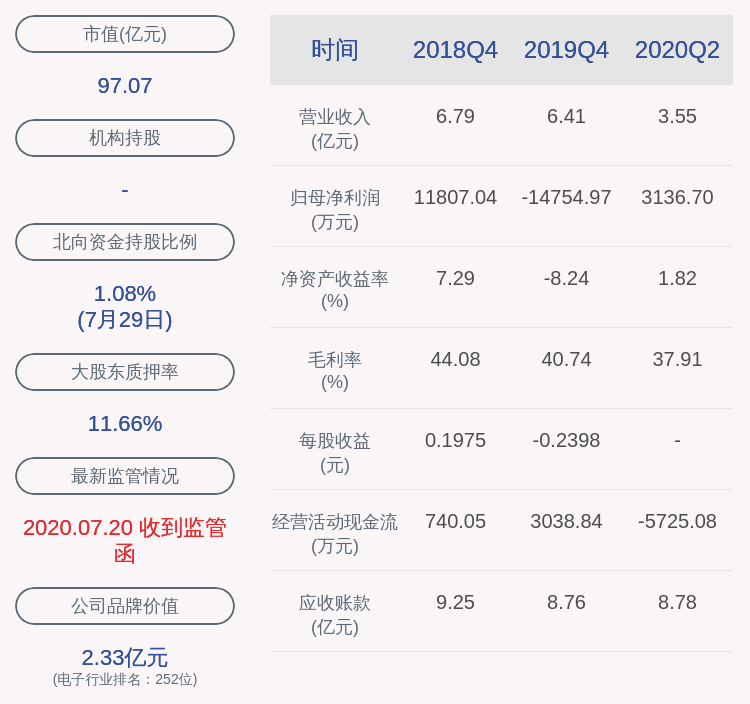张全胜|HAYA乐团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地方叫草原( 四 )
只有黛青塔娜自己知道她在干什么 。 不开灯 , 屋内一点点光 , 自己一个人光脚待着 , 一天半瓶酒咚咚咚地灌下去 。 酒要喝到正正好 , 不能多也不能少 , 喝到整个人状态松弛神经活跃但身体尚可掌控时 。 不能听原曲 , 但可以听点别的音乐 , 为的是不被固有的东西牵着走 , “不能应付 , 要给这个歌一个重新的定义 。 ”
大概熬了一礼拜 , 闭关的最后半小时 , 黛青塔娜彻底兴奋:“我写出来词了!”下楼给全胜一念 , 全胜起了满身的鸡皮疙瘩 , 心想:成了 , 这个事应该是可以成了 。
黛青塔娜把这个闭关的过程视为“跟自己相处” 。 这些年里她总在找自我——失落找回是反复的过程 , 找到了安静的A面不够 , 还需要她释放狂野的B面 。 《寂静的天空》后 , 为了录更有力量感的新专辑《迁徙》 , 张全胜把当时还不太放得开的黛青塔娜带到学校操场主席台上 , 说 , 你就在这练 。 操场上有不少跑步锻炼的人、上体育课的大学生 , 塔娜扭捏着说自己不好意思 , 心里想的是张全胜简直疯了 。
张全胜不管 , 站在台下给塔娜录视频 。 他知道日本有一种超市销售 , 就是要站在大街上使劲喊 , 把他人的眼光都忘掉 , 只去尽力表达自己 , “这时候你才能冲破自己内心的束缚 。 ”
塔娜的B面确实越来越好 。 而和来自不同国家、族群的朋友们一起玩音乐的过程 , 也让她、让HAYA的每个人都越来越放松 。 他们和朋友的聚会常常会变成一场世界音乐的狂欢——就在不久前 , 他们在中央民族大学附近一家普通的火锅店里聚餐 , 朋友们分别来自维吾尔族、蒙古族、苗族、非洲、以色列 , 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乐器 。 一说要即兴表演 , 一开始还是你推我让规规矩矩 , 结果酒越喝越多 , 喝到最后屋子里各种乐器歌声轰隆作响 。
“有一个苗族小伙是吹芦笙的 , 但那天没带 , 听到音乐的时候 , 贼着急贼兴奋 , 一直在唱歌 , 唱他自己苗语的调 。 前面大家还让一让 , 到最后实在争不过了 , 直接冲到前面开始喝啤酒 , 到后面就已经倒立了 。 ”
说起那倒立的苗族小伙 , HAYA所有人都哄然大笑起来 , 争着表演那男孩倒而立面红耳赤的样子 。
某种程度上 , 这也越来越接近黛青塔娜内在自我的释放 。 “我总是内心有一种想要喊出来的声音 , 这个东西一直还没有消失 , 我不想把它藏起来 。 ”
本文图片
迁徙与呐喊
出于同样的原因 , 为《乐队的夏天》选歌时 , 第一首在黛青塔娜心里浮现出来的 , 其实是《迁徙》 。
《迁徙》的尾声 , 是一声似要撕破天空的嘶鸣 , 紧接着一片空寂 , 再慢慢响起马头琴的无奈与沉默 。 有乐迷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现场时 , 形容自己直接听傻了 , “灵魂好像被震了出来 。 ”
第一次为这首歌写注解时 , 黛青塔娜曾写下这样的文字:
“候鸟迁徙 , 为了生命的呼吸 , 候鸟迁徙 , 为了生命的延续 , 牧人迁徙 , 为了天地的生生不息 。 我们迁徙要向着何方?当山崩裂出疼痛的伤口 , 大地露出他黑色的血液 , 这凝固的土地刺痛了双脚 。 是什么唤醒了我们毁灭的力量?是什么让我们永远都不知道满足?”
“迁徙是什么 , 我的祖先千百年都在迁徙 , 他们像山一样沉默 , 像草一样谦卑 , 像鹰一样自由 。 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 我们和这个世界一起走向了荒漠 。 ”
【张全胜|HAYA乐团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地方叫草原】音乐中的HAYA像是与这个世界同频 , 疼痛和紧促 , 悲伤与喜乐 , 俱是一体 。 黛青塔娜已经完全学会用自己的方法发声 , 曾经那些让她无比排斥的西方发声方法 , 也开始为她所用 。 她相信头顶三尺有神灵 , 每天早上 , 她会点上从家乡带来的柏香 , 拿到楼顶 , 让缭绕的烟气一直升到天上 , 然后吹海螺 , 祈祷 , 念经 。 整个乐队上台前 , 他们也会习惯性地敬地敬祖先 , 塔娜照例祈祷、燃香 , 所有人把状态沉下来 , 以一种近乎神秘的方式进入全然忘我的舞台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