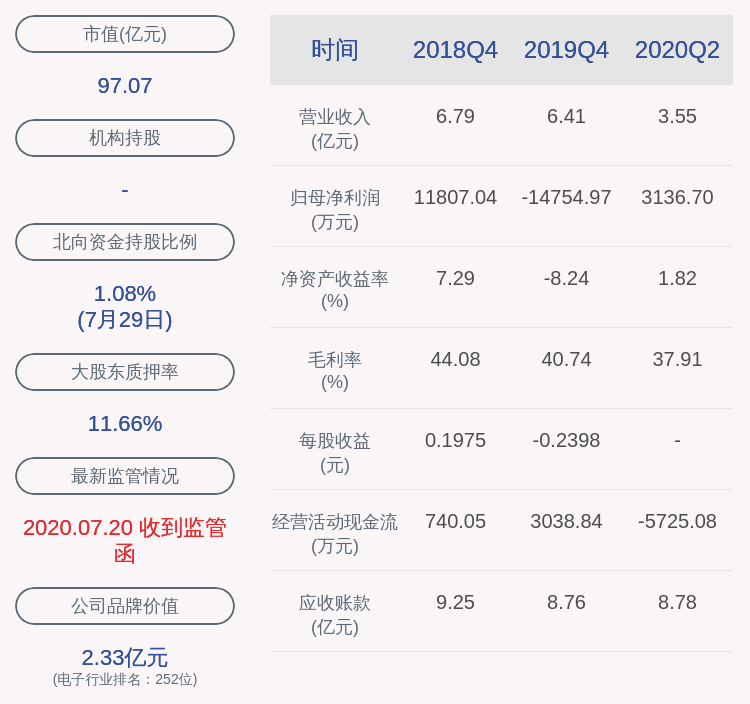张全胜|HAYA乐团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地方叫草原( 二 )
然而光鲜背后 , 是身体的疲惫和虚无 。 他隐约感到 , 这似乎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 不是他想要的音乐的感觉 。 在日本演了六百多场演出后 , 有一次他终于病倒 , 被诊断为先天性心脏病 。 自那以后 , 他形容自己的生活发生了一个又一个的爆炸 。 再然后 , 他放弃了13年的房子、车和存款 , 重新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人 。
那时他得了严重的抑郁症 , 一到下午四五点 , 手心出汗、心慌 , 感觉灵魂被抽走、意识消失 , 是濒死般的感觉 。 后来他租了一个30平米的小房子 , 一个人过了一段没有演出没有钱的生活 , 每天问自己:“我是谁 , 我从哪里来 , 究竟我要走什么样的路才是我自己的路 ,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的生命应该怎么度过?”
HAYA乐团便在这样的情境下诞生了 。 在蒙语里 , “HAYA”的意思是边缘 。 张全胜的血管里流着蒙古族的血液 , 但他并不愿把自己局限在蒙古族的音乐里 , 以此为根基 , 他希望更多元的音乐一起融合 , 不分族群、不分地域 , 消弭国别地界 , 创造出更新的一种音乐形式——这是他理解中的“世界音乐” 。
要融合不同民族与现代的乐器并不容易 。 民族乐器不如西洋乐器标准化 , 比如马头琴 , 天气、温度、湿度都会影响弦的调音 , 如果不做改良调整 , 在不同乐器之间调和音调、音色就是一件不可控的事情 。 HAYA第一次开演唱会时 , 本来上场前已经给蒙古族的弹拨乐器对好弦 , 结果演出一开始 , 键盘还是定好的调 , 弹拨乐器却突然高了小三度 , 马头琴也变高了二度 。
“整个就不在一个调里面!”张全胜摇头 。
除了民族乐器的改革 , 音乐风格的找寻也是大问题 。 录第一张专辑《狼图腾》时 , HAYA全员都是男性 , 音乐风格相较如今更为实验性 , 无论听众还是亲朋 , 给到的反馈几乎都是疑惑:“哎你为什么要做这种音乐呢?为什么不唱大家都能听得懂的那样一种音乐?”
张全胜心想不对 , 这绝不是他想要找寻的声音 。
本文图片
张全胜
迷失与寻找
黛青塔娜那时还只是HAYA的文案 , 偶尔伴唱 。
18岁时 , 她从青海考去了北京 , 进了中央民族大学声乐系 , 却不会唱歌了 。 学校教授的是一整套让她感到陌生的西方发声方法 , 她依草原传统学来的蒙古长调唱法 , 被老师认为是错误的 , “喊来喊去的 。 ”
塔娜在这大城市里迷了路 。 她的祖父母、父母都曾是部落里最好的歌者 。 小时候的塔娜其实特别不爱听妈妈唱歌 , 因为“和电视里唱的不一样” , 不时尚 。 但回想起来 , 那时的母亲已经开始在搜集民歌了 。 母亲拿着黑砖头般的大录音机 , 拿着哈达、酒和礼物 , 骑着马到草原上找还会唱民歌的老人 。 老人们也已经很长时间不唱了 , 得一直和他们聊天、喝酒、聊过往 , 聊着聊着才可能忽然想起某首歌就唱起来 。
母亲最后录出来的全是碎片 , 每个人唱的感觉都不一样 , 她会把同一首歌的各种版本一点点凑出来 , 然后自己模仿着唱 , 就这样录了一盘磁带 。
直到长大后黛青塔娜才明白母亲做这件事的意义 , 也开始向母亲去学那些生长于草原的歌 。 那些草原上的传统 , 怎么就错了呢?
迷失的也许不只是声音 。 大二那年回家 , 她刚学会化妆 , 一身时髦打扮回家 , 揣着“想让大家看我是从北京回来的大学生”的小心思 。 和爸爸一起回家的路上遇见牧民 , 牧民用不甚流利的汉语问 , 你是他的女儿吗?
塔娜说是的 。 牧民说 , 他也有个女儿 , “我的女儿是草原上的一匹野马 。 ”
这句话一下子把塔娜震住了 。 说不出是什么感觉 , 有羞愧 , 有反思 , 总之 , “他把我给弄醒了 。 ”
无论她自己还是张全胜 , 都会直言不讳地回忆那时的塔娜“唱歌很难听” 。 塔娜第一次试音时 , 张全胜亦毫不犹豫地在心里划下了否定线 。 好在因为文字美 , 塔娜作为HAYA的文案留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