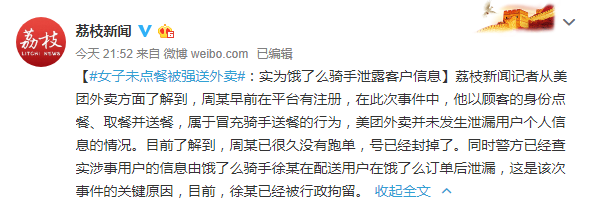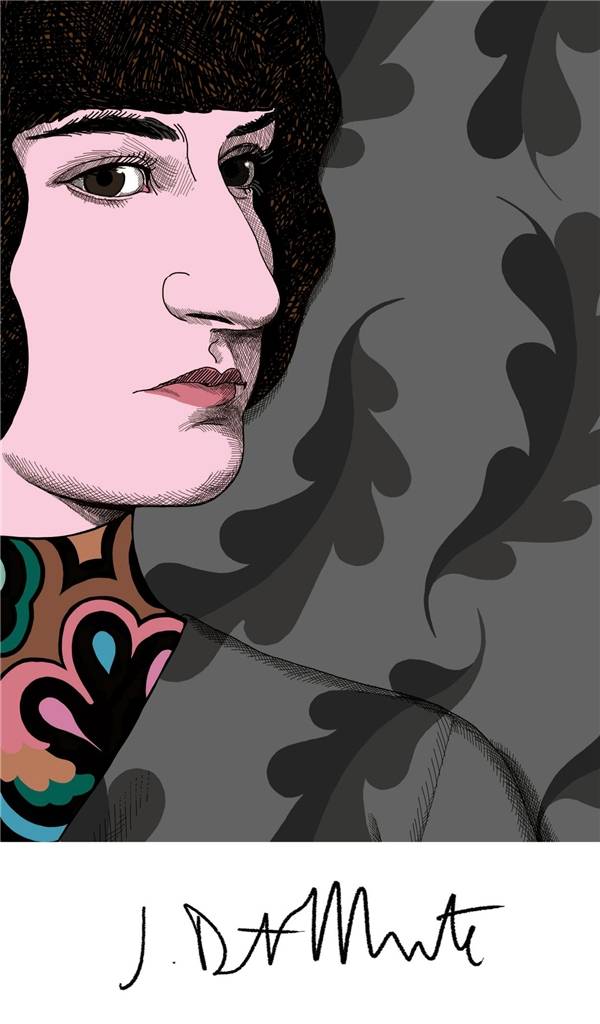гҖҺеёғйІҒе§ҶгҖҸеј еұҸз‘ҫ | еёғйІҒе§ҶпјҡиҜ—жӯҢеҰӮдҪ•еҜ№жҠ—еҚ•и°ғжҖ§пјҹ( еӣӣ )
иҖҢеңЁйқһиЈ”зҫҺеӣҪиҜ—дәәжқ°дјҠ?иө–зү№иә«дёҠ пјҢ еёғйІҒе§ҶжӣҙжҳҜеҠЁз”ЁдәҶжү№иҜ„家зҡ„е…ЁйғЁеҚҡеӯҰе“ҒиҙЁд»ҘеҸҠиғҪиЁҖе–„иҫ©жүҚиғҪ пјҢ жһҒиҫӣиӢҰең°жҢ–жҺҳиө–зү№иҜ—жӯҢзҡ„зҫҺеӯҰжёҠжәҗ пјҢ иҝҷеҪ“然дёҺиө–зү№зҡ„иЎҖз»ҹзӣёе…і гҖӮ жӯЈеҰӮ гҖҠжқ°дјҠВ·иө–зү№гҖӢдёҖзҜҮејҖеӨҙж—¶жүҖжҸҗеҲ°зҡ„ пјҢ иө–зү№зҡ„жүҖжңүиҜ—жӯҢжңүеҰӮдёҖж”ҜвҖңеҮҢжіўиҲһвҖқ пјҢ йӮЈжҳҜдёҖз§ҚиҘҝеҚ°еәҰзҫӨеІӣзҡ„иҲһи№Ҳ пјҢ иҲһиҖ…еңЁдёҖж №йҖҗжёҗйҷҚдҪҺзҡ„жқҶдёӢиЎЁжј” пјҢ зӣҙеҲ°еҸҳжҲҗвҖңиңҳиӣӣдәәвҖқ пјҢ еҸҢиҮӮеҸҢи…ҝеј ејҖж”Ҝиө·иә«дҪ“ гҖӮ йҳҗйҮҠиҖ…и®ӨдёәеҮҢжіўиҲһе’ҢеҸҜжҖ•зҡ„д»ҺйқһжҙІеҲ°зҫҺжҙІзҡ„еҘҙйҡ¶иҙёжҳ“зәҝи·ҜвҖңдёӯеӨ®иҲӘи·ҜвҖқжңүе…і пјҢ йӮЈж—¶еҘҙйҡ¶жҢӨеңЁйқһеёёзӢӯзӘ„зҡ„з©әй—ҙйҮҢ пјҢ д»ҘиҮідәҺ他们жҠҠиҮӘе·ұжүӯжӣІжҲҗдәәеҪўиңҳиӣӣ гҖӮ еёғйІҒе§Ҷи®Өдёә пјҢ еңЁжқ°дјҠ?иө–зү№зҡ„иүәжңҜйҮҢ пјҢ еҮҢжіўиҲһжҳҜдёәиҝҷдҪҚиҜ—дәәзҡ„зҫҺеӯҰдәӢдёҡеҮҶеӨҮзҡ„дёҖдёӘйҡҗе–» пјҢ йҖҡиҝҮеҶҷвҖңиҲӘи·Ҝзҡ„ж—Ҙеҝ—вҖқ пјҢ жҺўеҜ»зҰ»ејҖвҖңдёӯеӨ®иҲӘи·ҜвҖқзҡ„йҖҡйҒ“ гҖӮ дҪҶжҳҜ пјҢ еёғйІҒе§Ҷ马дёҠе°ұеҒҸзҰ»дәҶиҝҷж ·дёҖдёӘж–ҮеҢ–еҺҶеҸІдё»д№үзҡ„иҲӘеҗ‘ пјҢ иҖҢиө°еҗ‘ж–ҮеҢ–и°ұзі»еӯҰзҡ„жҺўзҙў пјҢ д»–жҺўз©¶вҖңз»“еҜ№вҖқеңЁиҘҝйқһеӨҡиҙЎзҘһиҜқдёҺеҹәзқЈж•ҷ пјҢ дёӨз§ҚдёҚеҗҢзҡ„е®—ж•ҷдёҺзҫҺеӯҰжёҠжәҗдёӯзҡ„йҡҗз§ҳеҜ№жҺҘ пјҢ д»ҺиҖҢе°Ҷжқ°дјҠ?иө–зү№еҪ’е…ҘдәҶиҘҝж–№иҜ—еӯҰдј з»ҹ гҖӮ еёғйІҒе§Ҷи®Өдёә пјҢ иө–зү№жҳҜдёҖдҪҚдјҹеӨ§зҡ„е®—ж•ҷиҜ—дәә пјҢ д»–зҡ„зІҫзҘһд№ӢзҪ‘иһҚеҗҲдәҶйқһжҙІгҖҒзҫҺжҙІе’Ң欧жҙІзҡ„зәҝзҙў пјҢ иҝҷеј зҪ‘дёӯзҡ„зҫҺжҙІйғЁеҲҶжҳҜж–°еўЁиҘҝе“Ҙе·һе’ҢеўЁиҘҝе“Ҙзҡ„ пјҢ 欧жҙІжҳҜдҪҶдёҒејҸзҡ„ пјҢ иҖҢйқһжҙІеҹәжң¬дёҠжҳҜеӨҡиҙЎдәәзҡ„ гҖӮ д»–жүҝи®ӨзҗҶи§Јжқ°дјҠ?иө–зү№зҡ„еӣ°йҡҫ пјҢ дҪҶд»–жӣҙж„ҝж„Ҹе°ҶиҝҷдёҖеӨҚжқӮиҖҢеӣ°йҡҫзҡ„еӣҫжҷҜзҗҶи§ЈдёәзәҜзІ№зІҫзҘһжҖ§зҡ„ пјҢ иҖҢжІЎжңүе°Ҷиҝҷеј еӣҠжӢ¬йқһжҙІгҖҒзҫҺжҙІдёҺ欧жҙІзҡ„зҪ‘еӣҫиҝӣиЎҢең°зјҳж”ҝжІ»ж„Ҹд№үдёҠзҡ„йҮҚжһ„ пјҢ з”ұжӯӨ пјҢ иҝҷж ·дёҖдҪҚйқһиЈ”зҫҺеӣҪдәәеңЁд»–笔дёӢжҲҗдёәдәҶвҖңдёҖдҪҚе…·жңүдёӯеҝғең°дҪҚзҡ„зҫҺеӣҪиҜ—дәә пјҢ дёҖдҪҚи¶ід»Ҙе’ҢзәҰзҝ°?йҳҝд»ҖиҙқеҲ©гҖҒA.R.йҳҝи’ҷж–Ҝд»ҘеҸҠдёәж•°дёҚеӨҡзҡ„еҒҘеңЁзҡ„иҜ—дәәеӘІзҫҺзҡ„зҫҺеӣҪиҜ—дәә гҖӮ вҖқиҫғзҹӯе°Ҹзҡ„гҖҠе·ҙеӢғзҪ—В·иҒӮйІҒиҫҫгҖӢж¬ дёӢзҡ„и§ЈйҮҠ пјҢ еңЁдёӨдёҮеӯ—зҡ„гҖҠжқ°дјҠВ·иө–зү№гҖӢдёҖзҜҮйҮҢеҫ—еҲ°дәҶиЎҘеҒҝ пјҢ ж— и®әдҪ жҳҜеҗҰеҗҢж„Ҹиҝҷз§Қи§ӮзӮ№ пјҢ йғҪеҸҜд»ҘиҜ»еҮәеёғйІҒе§Ҷдёәд№Ӣд»ҳеҮәзҡ„зҫҺеӯҰиҖғиҫЁе·ҘдҪңдёҠжүҖеҮқз»“зқҖзҡ„жҷәж…§дёҺжұ—ж°ҙ гҖӮ
жң¬ж–ҮжҸ’еӣҫ
е“ҲзҪ—еҫ·В·еёғйІҒе§ҶпјҲ1930-2019пјү
гҖҠиҜ—дәәдёҺиҜ—жӯҢгҖӢз”ұжӯӨеұ•зҺ°дәҶеёғйІҒе§ҶеңЁиҜ—еӯҰжү№иҜ„дёӯзҡ„еҗ„з§Қе°қиҜ• пјҢ д»–жІЎжңүиҜ•еӣҫеӣһйҒҝе…·дҪ“й—®йўҳ пјҢ зӣёеҸҚ пјҢ з”ұдәҺеҜ№жүҖйҖүжӢ©зҡ„иҜ—дәәеҜ№иұЎзҡ„еҝ е®һ пјҢ дҪҝеҫ—иҮӘе·ұдёҖж¬ЎеҸҲдёҖж¬Ўең°йқўдёҙйҳҗйҮҠдёҠзҡ„з§Қз§Қйҷ©еўғ пјҢ д№ҹе°ҶеҮ д№ҺжүҖжңүдёҺиҜ—жӯҢжңүе…ізҡ„зҫҺеӯҰй—®йўҳ пјҢ жё…жҷ°ең°е‘ҲзҺ°еңЁиҜ»иҖ…йқўеүҚ гҖӮ дёҚиҝҮ пјҢ еңЁжҖҖзқҖе·ЁеӨ§зҡ„зҗҶи®әеҙҮ敬д№ӢеҝғиҜ»е®Ңе…Ёд№Ұд»ҘеҗҺ пјҢ иҜ»иҖ…дјҡеҸ‘зҺ° пјҢ еңЁеёғйІҒе§ҶйӮЈдјҹеӨ§зҡ„йҳҗйҮҠиҖ…зҡ„иә«еҪұд№ӢдёӢ пјҢ иҜ—жӯҢзҡ„еҮәеҸ‘зӮ№жҳҜдёӘдәәзҡ„ пјҢ еҸҲз»Ҳе°ҶеӣһеҲ°дёӘдәә гҖӮ ж–Ҝи’Ӯж–ҮжЈ®з§°иҜ—жӯҢдёәеҶ…еҝғжҡҙеҠӣ пјҢ иҜҙеҸҜд»Ҙз”Ёе®ғжқҘжҠөеҫЎеӨ–йғЁдё–з•Ңзҡ„жҡҙеҠӣ гҖӮ еёғйІҒе§ҶеҲҷиҜҙ пјҢ иҜ—жӯҢзҡ„еҠҹиғҪеңЁдәҺи®©жҲ‘们еӯҰдјҡзҶ¬иҝҮеҝ…е°ҶжқҘдёҙзҡ„жӯ»дәЎ пјҢ жҲ–иҖ…жҠҠжҲ‘们ж·ұзҲұзҡ„йҖқиҖ…дәӨиҝҳз»ҷжҲ‘们 гҖӮ вҖңиҜ—жӯҢж— жі•еә”еҜ№зӨҫдјҡйЎҪз–ҫ пјҢ дҪҶе®ғеҚҙеҸҜд»Ҙз–—ж•‘иҮӘжҲ‘ пјҢ жІЎжңүе…¶е®ғдёңиҘҝиғҪз»ҷжҲ‘们еёҰжқҘиҝҷз§Қе®үж…°дёҺз–—ж•‘ гҖӮ вҖқжҲ‘жғі пјҢ иҝҷе°ұжҳҜд»–е§Ӣз»ҲиҰҒз»ҙжҠӨиҜ—жӯҢзҡ„иҮӘи¶іжҖ§зҡ„еҺҹеӣ пјҢ дёҚж„ҝж„ҸиҜ—жӯҢеңЁд»»дҪ•дёҖз§ҚдёҚиғҪд»Өд»–ж»Ўж„Ҹзҡ„и§ЈиҜ»жі•д№ӢдёӢзғҹж¶Ҳдә‘ж•Ј пјҢ е“ӘжҖ•иҝҷз§Қз»ҙжҠӨе·Із»ҸеҸҳжҲҗдәҶдёҖз§ҚжӢ’з»қ гҖӮ еҪ“жӯӨд№Ӣж—¶ пјҢ гҖҠиҜ—дәәдёҺиҜ—жӯҢгҖӢзҡ„дёӯиҜ‘жң¬й—®дё– пјҢ иҖҢеёғйІҒе§ҶеҲҡеҲҡзҰ»ејҖзҡ„иҝҷдёӘдё–з•Ң пјҢ е°ұдёӘдҪ“иҖҢиЁҖ пјҢ з–ҫз—…дёҺеҶ…еҝғз–—ж•‘й—®йўҳеҸҲйҮҚж–°жҲҗдёәдәҶе…ЁзҗғжҖ§зҡ„з—ҮеҖҷ пјҢ йӮЈд№ҲжҲ‘们没жңүзҗҶз”ұдёҚеҶҚйҮҚж–°жҖқиҖғдёҖдёӢ пјҢ еёғйІҒе§ҶејҸзҡ„зҫҺеӯҰж ҮеҮҶдёҺзҫҺеӯҰжӢ’з»қд№Ӣеҫ—еӨұжүҖеңЁ гҖӮ
2019е№ҙ12жңҲ19ж—Ҙ
2020е№ҙ3жңҲ30ж—Ҙдҝ®ж”№
жҺЁиҚҗйҳ…иҜ»
- пјҡдёәдҪ•иҜҙдёӯеӣҪиҜ—жӯҢзҡ„ж ёеҝғжҳҜж„ҸеўғиүәжңҜпјҹд»Җд№ҲжҳҜж„ҸиұЎпјҹд»Җд№ҲжҳҜж„Ҹеўғпјҹ
- гҖҺгҖҸз»ҙеӨҡеҲ©дәҡеәҶ46еІҒз”ҹж—Ҙ з§°жғіеҝөеӨ§е„ҝеӯҗеёғйІҒе…Ӣжһ—
- гҖҺеӨ§жҙӢиҜ—жӯҢгҖҸеӨ§жҙӢиҜ—жӯҢпјҡжҲ‘们пјҢеҶҚж¬ЎзЎ®и®ӨдёўеӨұзҡ„еЈ°йҹіпјҢеғҸзЈ·е…үпјҢжҳ е°„зқҖиҜҜе…Ҙзҡұзә№зҡ„йқ’жҳҘгҖҠеӨҸж—ҘйЈһйёҹгҖӢгҖҠеҶ¬еҺ»жҳҘжқҘгҖӢ
- ең°зҗғи°ЈпјҡеӨ§жҙӢиҜ—жӯҢпјҡең°зҗғи°ЈгҖҠең°зҗғи°ЈгҖӢгҖҠеҺҹжқҘжҳҜдёҖеҸӘз”»зңүйёҹпјҢеғҸдҪ йӮЈж ·зҲұж’’еЁҮпјҒгҖӢ
- гҖҺзҝҹж°ёжҳҺгҖҸдёҖдёӘеҢ—ж–№зҡ„дёҠеҚҲпјҢжҖқеҝөзқҖдёҖдёӘдәәпјҢжҲ‘жҳҜдёҖдәӣиҜ—жӯҢиҚүзЁҝпјҢдҪ жҳҜдёҖйҰ–иҜ—
- гҖҗж·ұеңіж–ҮеӯҰгҖ‘еёёеҫ·пјҢйӮЈеә§иҜ—дёӯзҡ„еҹҺпјҲеҺҹеҲӣиҜ—жӯҢпјҢзғӯжғ…жҙӢжәўпјҢдјҳзҫҺеӨ§ж°”пјҒпјү
- гҖҺиҜ—жӯҢгҖҸиҚҗиҜ»||гҖҠдёүеәҰиҜ—зӨҫгҖӢжңҖзҫҺжғ…иҜ—зІҫзј–пјҲ收и—ҸзүҲпјү
- гҖҺйӣӘзҹігҖҸйӣӘзҹіеҺҹеҲӣиҜ—жӯҢгҖҠеҗүзҘҘеҝ«д№җгҖӢ
- гҖҢиҜ—жӯҢгҖҚгҖҗиҜ—дәәжңүзәҰгҖ‘иӢҘе°ҳпјҡжҳҘеӨ©пјҢжҠҠеҝғжү“ејҖ
- еӨ§жҙӢиҜ—жӯҢпјҡеӨ§жҙӢиҜ—жӯҢпјҡжҲ‘иҝңеңЁиҚ’йҮҺпјҢд»ҺдёҚиҜҙзҲұпјҢеҚҙжҜ”и°ҒйғҪд№–......гҖҠ2:斑马пјҢзҫҡзҫҠгҖӢгҖҠ3:иқҙиқ¶пјҢиң»иң“гҖӢгҖҠ4:дә‘жңөпјҢз«–зҗҙгҖ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