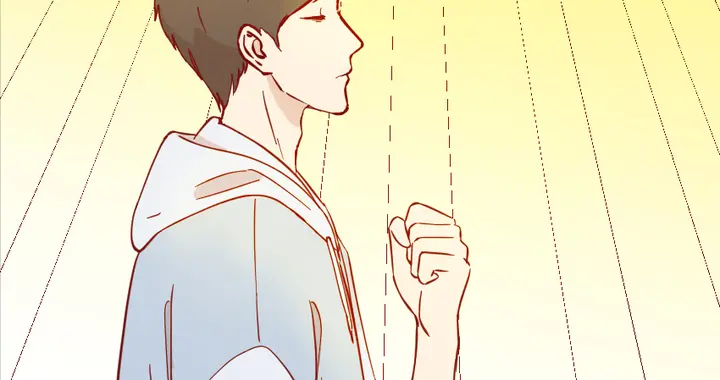1990年6-8月,时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樊锦诗率考古小组在龟兹石窟考察,我是小组中的一员 。8月初 , 宿先生参与的“丝绸之路沙漠路线第一次考察团”踏查克孜尔石窟 。那天先生见到我后,说:李裕群已经考回北大 , 你有什么打算?我马上实话实说:这次来库车前,我在敦煌莫高窟接待了印度驻华大使任嘉德(C.V. Ranganathan) 。在参观洞窟的过程中,任大使获悉我做佛教考古,答应从印度政府找奖学金资助我去印度留学 。而去年(1989年)下半年,芝加哥大学斯德本(Harrie H. Vanderstappen)教授来信还是希望我去美国读博士 。在这种情况下 ,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宿先生说:如果你还想继续从事佛教考古,那就应该去印度源头看看,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好的机会 。芝加哥大学的情况我知道,到北京大学继续深造你也还有机会 。这次先生对我的劝勉,增强了我去印度进修佛教考古的决心 。因为研究佛教文化遗产的来龙去脉,尤如勘测一条河流;要想了解其全貌 , 不但要看中游和下游,而且必须考察上游 。这样,才能对其有一总体印象 。为了赴印留学,我启程前做了一些专业准备,但当时在敦煌研究院能找到的印度佛教考古和佛教艺术方面的资料相当有限 。1991年7月,我开始在(印度)英迪拉甘地国立艺术中心(Indira Gandhi National Centre for the Arts)进修 。经过一段考察和学习,我打算在印度德里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但做什么题目有点拿不准 。为此,我专门写信给宿先生 。先生回信希望我做古代天竺地面佛寺或者阿旃陀石窟研究,并随信附了一份相关考古书目 。应该说,宿先生所附印度佛教考古书单的大部分我那时都有了一定了解,但在我赴印度留学之前则多不知晓 。我为先生阅读范围之广敬佩得五体投地,因为宿先生并不研究印度地面佛寺和石窟寺,他怎么会看过这么多专业书籍呢?按照先生指示 , 我先把有关材料找来阅读 , 然后在同年11月系统调查了印度北部地区的地面佛寺遗址 , 结果发现不好做深入、系统的研究,因为有些较重要的佛寺遗址没有做过正规的考古发掘 , 如与西藏桑耶寺关系密切的阿旃延那布尼或欧丹多补黎(Odantapuri/ Udda??apura)佛寺遗址就找不到任何考古发掘资料 。至于说阿旃陀石窟,经过阅读前人论著 , 发现作为后学我要与欧美同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无法发挥我的汉文文献优势 。最后,经与宿先生商量并征得印度导师同意,选择以塔庙窟为中心做中印两国石窟寺的比较研究 。
1998年,北京大学经历了百年校庆,宿先生彼时心情相当愉悦 。校庆后,先生曾写过一幅字:“中国佛学对外来佛典的阐述不断有创造性的发挥,形成中国独有的理论体系 。中国佛教艺术同样发展出符合自己民族精神特色的各种形象,需要我们进一步清理分析和深入探讨 。”实际上,宿先生在书写时并没有“分析”二字,等到赠予我时,先生觉得还应加上分析,最后以铅笔补入 。这幅训条一直指导我此后的佛教考古工作,尤其是关于中印佛教艺术的比较研究 。也是校庆后某一天 , 晚上我向先生请教完后陪他沿未名湖边小道散步,走了一圈之后 , 先生说:再走一圈吧 。我们边走边聊,后来谈到了二陈(陈寅恪、陈垣) 。先生说百年树人,不太容易再出现二陈了 。我当时年轻,就说:像您这样的考古学家是断前的,能否绝后难说,但恐怕百年之内不会再有 。稍停片刻 , 先生突然说了一句:“你以后写文章、发表东西要谨慎 , 别忘了你是我的学生!”

文章插图
宿白先生题字
2001年6月18-24日和12月22-25日,我在半年内两次陪同宿先生前往南京栖霞山考察 。其中,6月18日在北京-南京的飞机上,先生对我说:这次去南京,主要是帮助他们做栖霞山千佛崖考古报告 , 我们自己不写东西 。他向南京文物局等单位的同仁说:我们这次来,就是帮助大家尽快完成栖霞山千佛崖的正规记录并整理出考古报告 。先生向人介绍时,说我是他的助手,这既让我受宠若惊,也使我惶恐不安 。为了这部报告 , 我代表先生十年间赴南京栖霞山十几次 , 迄今没有专门写过栖霞山石窟的文章,尽管考古记录和报告中的不少内容都是我先口述、当地同行记录完成,所有千佛崖窟龛的测绘图也都经过我修改 。
2004年9月 , 为了实施龙门石窟擂鼓台区考古报告的组织 , 宿先生率领我们赴龙门石窟 , 按照他规划的课程全面培训“石窟寺考古报告培训班”学员 。他不仅具体讲解石窟寺考古报告工作的各项程序和必须严格遵循的学术规范及原则,而且特别强调:“档案工作是国家文物局对国保单位的基本要求,因为它既是本单位其他工作的基础 , 也是保护本单位重要文物的一种手段,它是为物质文化特别是地上遗迹残损或破坏后复原提供翔实资料,但目前还没有哪个单位能够真正完成全面系统的档案工作 。石窟寺是地面上的、重要的古代文化遗迹,是中国历史考古重要遗迹的一部分,因此石窟档案和考古报告都应当按照档案的内容和考古的要求来编写 。龙门石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后,其首要的、最基础的学术工作应当从石窟寺档案做起 , 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洞窟考古报告的编写 。”
推荐阅读
- 威廉和凯特结婚纪念日,官方发了一张黑白照
- 英王室最新消息:威廉王子取消和凯特的13周年结婚纪念日活动,确实危险
- 最稳妥的水桶机?小米10至尊纪念版一周体验报告
- 曝小S被大S拖累,无缘舒淇冯德伦结婚纪念日派对,没能跟孙芸芸玩
- 寒食节是纪念哪个人的 寒食节是纪念哪个人的呢
- 陈晓《火柴小姐和美味先生》开播就被五星刷屏,观众的好评理由出奇一致!
- 舒淇晒与冯德伦结婚纪念日合照
- 合肥渡江战役纪念馆在哪里 合肥渡江战役纪念馆预约电话
- 翁先生打一动物,“ 老人七十仍沽酒千壶百翁花门口”打一动物
- 张国荣逝世21周年,唐先生发文悼念配文引热泪,本人近照白发苍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