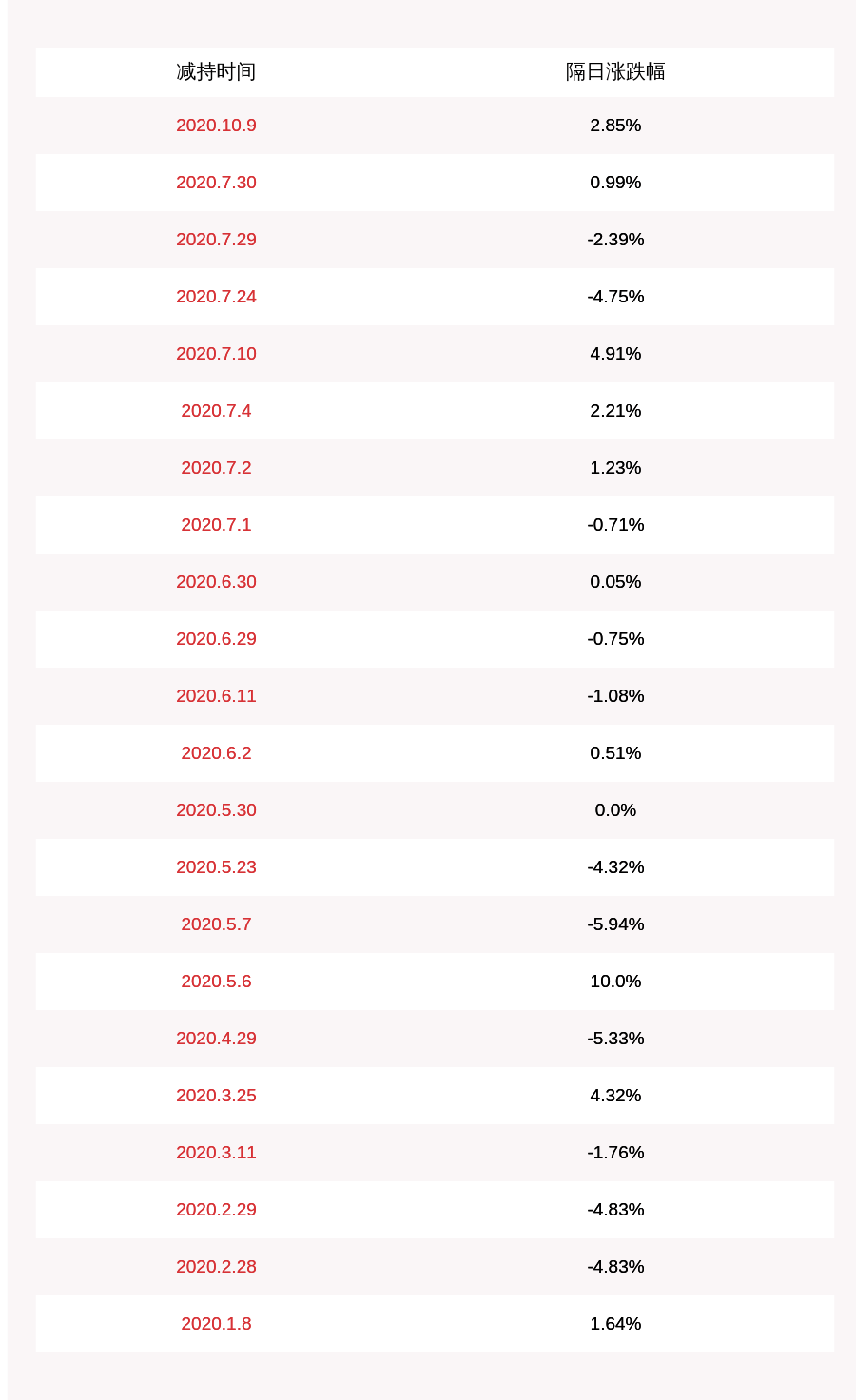еӯҰжңҜ|дјҠиҺұдј‘В·еҚЎиҢЁдёҺеӨ§дј—дј ж’ӯз ”з©¶пјҡеҚҠдёӘеӨҡдё–зәӘзҡ„еӯҰжңҜжј”еҸҳ( дёү )
еҰӮй»ҳйЎҝжүҖиҜҙпјҡвҖңзӨҫдјҡеӯҰиҖ…зҡ„жңҖз»Ҳзӣ®зҡ„жҳҜжё…жҷ°иЎЁиҝ°е…ідәҺзӨҫдјҡз»“жһ„еҸҠе…¶еҸҳиҝҒпјҢд»ҘеҸҠеңЁиҝҷдёҖз»“жһ„дёӯдәәзҡ„иЎҢдёәеҸҠе…¶з»“жһңзҡ„йҖ»иҫ‘дёҠзӣёдә’е…іиҒ”并дёәз»ҸйӘҢжүҖиҜҒе®һзҡ„е‘ҪйўҳвҖқгҖӮе®һзҺ°иҝҷдёҖзӣ®зҡ„зҡ„йҖ”еҫ„жӯЈжҳҜе°Ҷз»ҸйӘҢз ”з©¶дёҺдёӯеұӮзҗҶи®әзӣёз»“еҗҲзҡ„вҖңжі•е…ёеҢ–вҖқзҡ„иҝҮзЁӢпјҡвҖңеҜ»жұӮеңЁжҳҺжҳҫдёҚеҗҢзҡ„иЎҢдёәйўҶеҹҹе°ҶеҸҜз”Ёзҡ„з»ҸйӘҢжҰӮжӢ¬зі»з»ҹеҢ–вҖҰвҖҰе®Ўж…Һең°е»әз«ӢзӣёеҜ№жҡӮж—¶зҡ„еҒҮи®ҫпјҢд»ҘдҝқиҜҒжү©еұ•зҺ°жңүзҗҶи®ә并жҸҗеҮәиҝӣдёҖжӯҘзҡ„з»ҸйӘҢжҺўзҙўгҖӮвҖқжңҖз»ҲпјҢвҖңеҠҹиғҪеҲҶжһҗдҫқиө–дәҺзҗҶи®әгҖҒж–№жі•е’Ңиө„ж–ҷд№Ӣй—ҙзҡ„з»“еҗҲвҖқпјҢе…¶дёӯпјҢдёӯеұӮзҗҶи®әдёҚд»…жҳҜзәҜзІ№зҡ„з»ҸйӘҢжҰӮжӢ¬пјҢиҖҢдё”жҳҜеҢ…еҗ«дәҶдёҖз»„иғҪжҺЁеҜјеҮәз»ҸйӘҢжҰӮжӢ¬зҡ„еҒҮи®ҫпјҢвҖңеҺҹеҲҷдёҠеә”з”ЁдәҺзӨҫдјҡеӯҰдёӯеҜ№з»ҸйӘҢз ”з©¶зҡ„жҢҮеҜјвҖқ并дёҺзӨҫдјҡеӯҰзҗҶи®әдҪ“зі»дҝқжҢҒдёҖиҮҙгҖӮ
й»ҳйЎҝеңЁиҜҙжңҚз ”з©¶дёӯи·өиЎҢзҡ„зӨҫдјҡз»“жһ„еҲҶжһҗж·ұеҫ—вҖңжү№еҲӨзҗҶи®әеңЁзҫҺеӣҪдј ж’ӯз ”з©¶еңҲеӯҗйҮҢжңҖеј•дәәжіЁзӣ®зҡ„д»ЈиЎЁвҖқжҙӣж–ҮеЎ”е°”зҡ„ж¬ЈиөҸпјӣиҖҢй»ҳйЎҝд№ҹжҠ•жЎғжҠҘжқҺпјҢи®Өдёәжҙӣж–ҮеЎ”е°”вҖңз»јеҗҲж–№жі•зҡ„жҲҗеҠҹвҖқиҜҒжҳҺдәҶвҖңзӨҫдјҡе“ІеӯҰзҡ„еҫ·еӣҪжҖқжғійЈҺж јдёҺзҫҺеӣҪзҡ„ж–№жі•и®ә并йқһдёҚзӣёе®№вҖқгҖӮдёҚеҗҢдәҺйңҚе…Ӣжө·й»ҳпјҲMax Horkheimerпјүе®Ңе…ЁжӢ’ж–ҘеҜ№вҖңеҚ•дёӘвҖқеҸ—дј—иЎҢдёәиҝӣиЎҢз»ҸйӘҢз ”з©¶пјҢжҙӣж–ҮеЎ”е°”ејәи°ғиҮӘе·ұвҖңжғіеңЁз¬ҰеҗҲжү№еҲӨзҗҶи®әзҡ„еҗҢж—¶е®һзҺ°з§‘еӯҰдёҠжңүж„Ҹд№үзҡ„з ”з©¶е·ҘдҪңпјҢ并е°Ҷд№Ӣеә”з”ЁеҲ°ж”ҝжІ»зҺ°е®һдёҠвҖқгҖӮдҪ“зҺ°еңЁеӨ§дј—дј ж’ӯдёҠпјҢжҙӣж–ҮеЎ”е°”и®ӨдёәвҖңж•Ҳжһңй—®йўҳеҢ…еҗ«дәҶжҜ”ж¶Ҳиҙ№е®һиҜҒдё»д№үеҲҶжһҗжӣҙеӨҡзҡ„еҶ…е®№пјҢе®ғеҲәжҝҖ并鼓еҠұдәҶзҗҶи®әжҺўзҙўпјҢиғҪеӨҹеё®еҠ©з•Ңе®ҡж•Ҳжһңзҡ„вҖҳзӨҫдјҡеҶіе®ҡеӣ зҙ вҖҷпјҢеҪўжҲҗеҜ№дәҺвҖҳжӯЈејҸе’ҢйқһжӯЈејҸз”ҹдә§дёҺйҳ…иҜ»жҺ§еҲ¶еҪұе“ҚвҖҷзҡ„зҗҶи§ЈпјҢ并且з”ҹжҲҗеҜ№дәҺвҖҳжҠҖжңҜж”№еҸҳдёҺз»ҸжөҺе’ҢзӨҫдјҡеҗҺжһңвҖҷзҡ„иҜ„дј°вҖқгҖӮд»–е°ҶеҜ№еҲәжҝҖдёҺеҸҚеә”зҡ„вҖңзҗҶи§ЈвҖқдёҺ欧жҙІе“ІеӯҰйҒ—дә§иҒ”зі»иө·жқҘпјҢиҜ•еӣҫйҖҡиҝҮеҜ№еӨ§дј—еӘ’д»ӢеҸ—дј—еҠҹиғҪзҡ„з ”з©¶пјҢеҪўжҲҗеҜ№зӨҫдјҡзҡ„еҺҶеҸІжҖ§зҗҶи§ЈгҖӮжӯЈеӣ дёәжӯӨпјҢдёҺжӢүжүҺж–ҜиҸІе°”еҫ·е’Ңй»ҳйЎҝзҡ„зҹӯжңҹе…ҙи¶ЈдёҚеҗҢпјҢжҙӣж–ҮеЎ”е°”еҸҚеҖ’жҲҗдәҶеҜ№дј ж’ӯз ”з©¶е…ҙи¶ЈжҢҒз»ӯж—¶й—ҙжӣҙй•ҝзҡ„з ”з©¶иҖ…гҖӮ
жҙӣж–ҮеЎ”е°”иҝҷз§ҚдёҺжӢүж°ҸиҜқиҜӯзӣёдјјдҪҶзҹҘиҜҶйҖ»иҫ‘жҲӘ然дёҚеҗҢзҡ„вҖңиһҚеҗҲи§ӮвҖқжӣҙе…іеҝғйҖҡиҝҮеҜ№ж–ҮеӯҰзҡ„зӨҫдјҡеӯҰйҳҗйҮҠе°ҶдёӘдәәиЎҢдёәдёҺзӨҫдјҡгҖҒз»ҸйӘҢдёҺж„Ҹд№үгҖҒеҺҶеҸІдёҺзҺ°е®һз»“еҗҲиө·жқҘпјҢиҖҢйқһвҖңжҠҠиҮӘе·ұеұҖйҷҗеңЁзІҫеҜҶең°е®ҡд№үеҶ…е®№еҲҶжһҗгҖҒж•ҲжһңгҖҒеҸ—дј—еҲҶеұӮзӯүй—®йўҳдёҠвҖқгҖӮдёҚиҝҮпјҢе®һзҺ°иҝҷдёҖиһҚеҗҲзҡ„ж–№ејҸд№ҹжҳҜйҖҡиҝҮеә”з”Ёз ”з©¶е®ҢжҲҗзҡ„гҖӮеңЁдәҢжҲҳж—¶жңҹжҙӣж–ҮеЎ”е°”дёҺеӨ§еӨҡж•°дј ж’ӯеӯҰиҖ…дёҖиө·пјҢдёәжҲҳж—¶жғ…жҠҘеұҖпјҲOWIпјүд»ҺдәӢеҲҶжһҗеҫ·еӣҪе№ҝж’ӯеҶ…е®№зҡ„е·ҘдҪңгҖӮжҲҳеҗҺпјҢд»–жҲҗдёәзҫҺеӣҪд№ӢйҹіпјҲVOAпјүзҡ„з ”з©¶дё»з®ЎпјҢз ”з©¶зҫҺеӣҪе®ҳж–№е®Јдј еңЁеҶ·жҲҳд№ӢеҲқзҡ„ж•ҲжһңгҖӮд№ҹжӯЈжҳҜеңЁжӯӨжңҹй—ҙпјҲ1949-1954е№ҙпјүпјҢд»–ејҖе§ӢиҜ„дј°е№ҝж’ӯиҠӮзӣ®еңЁеӣҪйҷ…зҡ„еҪұе“ҚпјҢе°Ҷж•Ҳжһңз ”з©¶ж”ҫеҲ°дёҚеҗҢеӣҪ家дёҺж–ҮжҳҺиғҢжҷҜдёӢиҝӣиЎҢиҖғиҷ‘гҖӮиҝҷж ·пјҢзӨҫдјҡзҗҶи®әзҡ„жү№еҲӨз«ӢеңәгҖҒдәәж–Үдё»д№үдј з»ҹдёҺи·Ёж–ҮеҢ–жғ…еўғйғҪиў«жҙӣж–ҮеЎ”е°”зәіе…ҘеҲ°еә”з”Ёз ”з©¶дёӯпјҢд»–зҡ„з ”з©¶д№ҹеӣ жӯӨиў«з§°дёәвҖңд№ҹи®ёд»ЈиЎЁдәҶжү№еҲӨзҗҶи®әдёҺзҫҺеӣҪзӨҫдјҡ科еӯҰж–№жі•д№Ӣй—ҙжңҖеҝ«д№җзҡ„иҒ”姻вҖқгҖӮ
дәҢгҖҒвҖңжҗӯжЎҘвҖқпјҡж— жі•ж‘Ҷи„ұзҡ„еҠҹиғҪдё»д№үйҳҙеҪұ
дёҠж»‘
еӯҰжңҜеҫҖеҫҖжҳҜжҙ»з”ҹз”ҹзҡ„дј жүҝпјҢеҢ…еҗ«з§Қз§ҚиЎ”жҺҘзҡ„дҝЎжҒҜгҖӮж·ұеҸ—д»ҘдёҠдёүдәәеҪұе“Қзҡ„еҚЎиҢЁе°ҶеҸ—дј—з ”з©¶иһҚе…ҘжӣҙеӨҡзӨҫдјҡз»“жһ„дёҺж–ҮеҢ–жғ…еўғйқўеҗ‘пјҢеңЁж–№жі•дёҺи·Ҝеҫ„дёҠеҲҷеҜ»жұӮи·ЁеӯҰ科дёҺеӨҡдј з»ҹзҡ„еҜ№иҜқгҖӮиҮӘ1959е№ҙеӣһеә”иҙқйӣ·е°”жЈ®вҖңжһҜиҗҺиҜҙвҖқејҖе§ӢпјҢеҚЎиҢЁе°ұе°ҶзӨҫдјҡ科еӯҰдёҺдәәж–Үдё»д№үиһҚеҗҲдҪңдёәзӘҒз ҙж—©жңҹж•Ҳжһңз ”з©¶жЎҺжўҸзҡ„и·Ҝеҫ„пјӣеңЁжү©ж•Јз ”究е’ҢдҪҝз”ЁдёҺж»Ўи¶із ”з©¶дёӯиҝӣиЎҢеҲқжӯҘи·өиЎҢпјҢеҰӮе°Ҷжү©ж•Јз ”究解йҮҠдёәвҖңдёҺдәәзұ»еӯҰгҖҒж”ҝ治科еӯҰдёӯзҡ„зӨҫеҢәз ”з©¶гҖҒзІҫиӢұз ”з©¶е’ҢзӨҫдјҡеҝғзҗҶеӯҰзҡ„йӣҶдҪ“иЎҢдёәз ”з©¶е»әз«ӢиҒ”з»“вҖқпјҢд»ҘвҖңж„Ҹд№үзҡ„еҚҸе•ҶвҖқдҪңдёәиҝһжҺҘж»Ўи¶із ”з©¶дёҺж–ҮеҢ–з ”з©¶д№Ӣй—ҙзҡ„жЎҘжўҒпјӣжҠҠж–ҮеӯҰдёҺдәәж–Үи·Ҝеҫ„зҡ„дҪҝз”ЁдёҺж»Ўи¶іеә”з”ЁеҲ°ж–Үжң¬еҲҶжһҗдёӯпјҢжҳҫзӨәдёҚеҗҢж–ҮеҢ–иғҢжҷҜдёӢеҸ—дј—еӨҡе…ғеҢ–зҡ„и§Јз Ғпјӣд»ҘжӣҙеҠ еӨҚжқӮзҡ„з¬ҰеҸ·еӯҰгҖҒдәәзұ»еӯҰгҖҒзӨҫдјҡеӯҰзӯүйҮҚжҖқеӘ’д»Ӣж•ҲжһңпјҢе°ҶеӘ’д»ӢдёҺжӣҙе№ҝжіӣзҡ„жңүе…ізӨҫдјҡгҖҒжҠҖжңҜгҖҒе…¬ж°‘гҖҒиә«д»ҪдёҺж°‘дё»зӯүеҸҳеҠЁе…ізі»зҡ„е…¬е…ұдәүи®әиҒ”зі»иө·жқҘгҖӮ
еңЁиҝҷдёҖзі»еҲ—еҜ№зҹӯжңҹж•Ҳжһңз ”з©¶зӘҒз ҙзҡ„е°қиҜ•дёӯпјҢе…ій”®зҡ„дёҖжӯҘеҚіжҳҜдҪҝз”ЁдёҺж»Ўи¶із ”з©¶гҖӮж—¶йҖў1950 е№ҙд»Јжң«е’Ң1960 е№ҙд»ЈеҲқпјҢеӯҰз•ҢвҖңеҜ№жөӢйҮҸдәә们жҺҘ收еӨ§дј—еӘ’д»Ӣе®Јдј зҹӯжңҹж•Ҳжһңзҡ„жҲҗжһңеҮәзҺ°дәҶжҷ®йҒҚзҡ„еӨұжңӣвҖқпјҢиҖҢдҪҝз”ЁдёҺж»Ўи¶із ”з©¶вҖңеҸҚжҳ дәҶжҜ”ж•Ҳжһңз ”з©¶иғҪеӨҹеҫ—еҮәзҡ„жӣҙеҸҜйқ зҡ„д»ҺдёӘдәәеҸ—дј—з»ҸйӘҢдёҺи§Ҷи§’жқҘзҗҶи§ЈеҸ—дј—еҸӮдёҺеӨ§дј—дј ж’ӯзҡ„ж„ҝжңӣвҖқгҖӮеҰӮеҚЎиҢЁиҮӘе·ұиЎЁиҝ°пјҢдҪҝз”ЁдёҺж»Ўи¶із ”з©¶дёҚеҗҢдәҺзҹӯжңҹж•Ҳжһңз ”з©¶пјҢвҖңд»ҺзӣҙжҺҘж•Ҳжһңй—®йўҳпјҲвҖҳеӘ’д»ӢеҜ№дәә们еҒҡдәҶд»Җд№ҲвҖҷпјүиҪ¬з§»еҲ°вҖҳдәә们用еӘ’д»ӢеҒҡд»Җд№ҲвҖҷзҡ„й—®йўҳвҖқпјҢејәи°ғвҖңеҸ—дј—зҡ„дё»еҠЁжҖ§е’Ңзӣ®ж Үдё»еҜјжҖ§вҖқпјҢи®ӨдёәвҖңжҙ»еҠЁеӯҳеңЁдәҺдәә们еңЁи®ӨзҹҘе’ҢеҪ’еұһж„Ҹд№үзҡ„иҝҮзЁӢдёӯеҜ№дәҺеӘ’д»ӢдҝЎжҒҜзҡ„еҲӣйҖ жҖ§и§ЈиҜ»вҖқгҖӮд»ҘжӯӨдёәеҮәеҸ‘зӮ№пјҢжңүдәәжҖ»з»“еҚЎиҢЁдә”еҚҒдҪҷе№ҙеҸ—дј—з ”з©¶зҡ„еҹәжң¬з»“и®әе°ұжҳҜи®ӨдёәвҖңеӘ’д»ӢеҸ—дј—жҳҜдё»еҠЁдё”жү№еҲӨзҡ„пјӣд»ҘдёҚеҗҢж–№ејҸеҜ№дј ж’ӯдҪңеҮәеҸҚеә”пјӣ并且еҸ—дј—дё»еҠЁжҖ§жәҗдәҺз”ұе…¶жүҖеұһзҡ„зӨҫдјҡзҪ‘з»ңж”ҜжҢҒзҡ„е…ҲйӘҢдҝЎеҝөдёҺжҖҒеәҰвҖқгҖӮ
жҺЁиҚҗйҳ…иҜ»
- жўҒжҖқжҲҗзҡ„дәҢе©ҡеҰ»еӯҗпјҡеӯҰжңҜжҲҗе°ұдёҠжҜ”дёҚиҝҮжһ—еҫҪеӣ пјҢйӮЈе°ұзј–ж•…дәӢжҠ№й»‘еҘ№
- еҗҙз§Ӣиҫүпјҡд№…иў«еҹӢжІЎзҡ„еӯҰжңҜеӨ§е®¶ йҰ–еұҠе…ЁеӣҪеҗҙз§ӢиҫүеӯҰжңҜз ”и®ЁдјҡжҰӮиҝ°
- вҖңдәІж°‘вҖқпјҡзҺӢеӯҰиҰҒд№үжүҖеңЁ
- жҹіеҗ‘жҳҘпёұйҷҲйёҝжЈ®е…Ҳз”ҹзҡ„жё…д»ЈеӯҰжңҜеҸІз ”究
- еңЁ2020пјҢжҸӯйңІдёҚз«ҜгҖҒеҸҚжҖқвҖңе”Ҝи®әж–Үи®әвҖқпҪңе№ҙз»ҲеӯҰжңҜдәӢ件зӣҳзӮ№
- дёӯеӣҪеҪ“д»ЈжңҖе…·еӯҰжңҜд»·еҖјдёҺ收и—ҸжҠ•иө„жҪңеҠӣиүәжңҜ家вҖ”вҖ”еҲҳй•ҝе…ө
- йғ‘йҮ‘йӣЁвҖ”вҖ”дёӯеӣҪеҪ“д»ЈжңҖе…·еӯҰжңҜд»·еҖјдёҺ收и—ҸжҠ•иө„жҪңеҠӣиүәжңҜ家
- дёӯеӣҪеҪ“д»ЈжңҖе…·еӯҰжңҜд»·еҖјдёҺ收и—ҸжҠ•иө„жҪңеҠӣиүәжңҜ家вҖ”вҖ”иғЎе…ҙд№Ұ
- дёӯеӣҪеҪ“д»ЈжңҖе…·еӯҰжңҜд»·еҖјдёҺ收и—ҸжҠ•иө„жҪңеҠӣиүәжңҜ家вҖ”вҖ”з«ҘжӨҚжҳҺ
- вҖңйңңж»ЎйҫӣзәўвҖ”вҖ”еӮ…еұұзҡ„з”ҹе№ігҖҒжҖқжғідёҺеӯҰжңҜеұ•вҖқд»Ҡж—ҘејҖеұ•



![[жІіеҢ—]жҲ‘еӣҪвҖңйҖҖжӯҘвҖқжңҖеҝ«зҡ„зңҒд»Ҫпјҡз”ЁдәҶ15е№ҙж—¶й—ҙпјҢдәәеқҮGDPд»Һ11и·ҢеҲ°26](http://img88.010lm.com/img.php?https://image.uc.cn/s/wemedia/s/2020/fbe0e0d48ea3828657c15b92de13582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