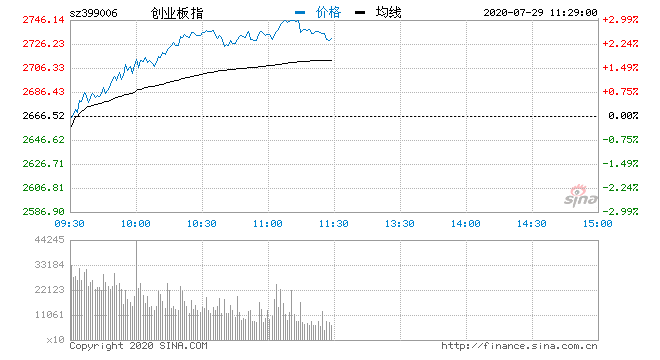新京报|《奥斯特利茨》与《土星之环》 湮灭的时间在现实中复活( 二 )
奥斯特利茨究竟恐惧什么呢?那就是与他这个名字密不可分的犹太人罹难史(奥斯特利茨是一个犹太村落 , 在将近一个半世纪之后 , 这里的居民都被移送特雷津集中营 。 巧合的是 , 名字来源于此的雅克·奥斯特利茨 , 他的母亲在40年代也被关押在此 。 这个名字的第二重含义 , 指的是巴黎的奥斯特利茨车站 , 雅克的父亲很可能正是在这个车站被押上了前往另一个集中营的列车;还是在这个车站附近 , 曾经积压着大量从犹太人那里掠夺而来的财产) , 被向上回溯到了一场拿破仑于1805年12月大败俄奥联军的战役 。
相比犹太人的遭遇 , 这场发生在第三次反法同盟战争期间的著名战役可能更具“公共性质” 。 由此 , 20世纪最黑暗的一页也就在关于这场战役事无巨细的描述中被遮蔽了 。 主人公不愿面对自己的名字 , 正如他所成长起来的那个社会早已在文明机制的运作下避开了这个名字映射的历史 , 而塞巴尔德写作此书的雄心壮志 , 毋宁说是要将这一事件的含义从公共领域恢复到独一无二的个体身上 。 失去的不是时间 , 而是被压抑、被清除、被改写的身份;恐惧的不是历史 , 而是人们在一个地点看到了并置其上的两重时间 。 正是通过这一别出机杼的对恐惧的描写 , 塞巴尔德成功地将原本作为一种时间艺术的小说 , 改造成了更倾向于雕塑或绘画的空间艺术 , 所以不再有命运的波澜壮阔 , 因为所有的命运都已告完成 , 它只是在那里等待着人们前去考古 。
让生者与逝者、往昔与现时和平共处
巴赫金曾经指出可视性对于歌德具有一种特殊意义:“一切重要的东西 , 都能够而且应该是可视的;一切不可视的东西也是不重要的”;“他不愿意(也不能够)把任何东西都看成是完成定型又静止不动的 。 他的眼睛不承认物体和现象只是简单地在空间中毗邻、单纯地共存 。 在任何静止不动、纷繁多样的事物背后 , 他都能看到不同的时间的存在……他把空间并列的东西分别归属于不同的时间阶段、不同的成长时代 。 ”这一观点之于塞巴尔德同样有效 。 也许正因后者吸收了歌德的可视性思想 , 他才得以在二十世纪行将结束时继续推进后现代主义未竟的使命:当线性的时间观念被拦腰斩断 , 小说这种有着根深蒂固时间属性的叙事艺术 , 如何去开拓未来?与唐·德里罗在《地下世界》中的路径相似 , 塞巴尔德同样选择将现代性宰制下的历史时间分割为两种:《奥斯特利茨》中是显性的公共历史与隐性的平民历史 , 《土星之环》里则是现时的时间与湮灭的时间 。 需要指出的是 , 后一本书中甚至不存在一个预后的、需要勘破的谜题 , 在同样是一个类似于作者的叙述者的漫游中 , 小说的叙事主线是“我”穿越英国萨福克郡的一次旅行 , 而所谓的谜题则是“我”在旅途中关于历史的玄思:一种看似随心所欲却相当庄重的平行联想 。
因此 , 在切分为十章的小说里 , 人们几乎找不到塞巴尔德之于叙事有何推进——如果有 , 那就是叙述者从一个地方漫游到了另一个地方 , 走走停停 , 观看以及冥想 。 但正文则一概是“我”在某地的现实景观中“看到”的过去:在一处近似废墟的海边平原 , 有个人对“我”谈起这里曾经转动的风车;萨默莱顿与洛斯托夫特也是如此 , 往昔繁华的庄园与城市而今早已破败不堪;曾经数量多到令人恐惧的鱼类以及不可阻挡的捕鱼业 , 在今天也已经变成了海洋坟墓的见证;在邓尼奇的荒野 , “我”意识到这里曾经存在着超过五十座的教堂、修道院和救济院……当然 , “我”也依次想到了与这些景观相关联的逝者:“我”的朋友迈克尔·帕金森、斯坦利·凯利 , 波兰裔英国作家康拉德与爱尔兰独立运动倡导者罗杰·凯斯门特 , 清帝咸丰、同治、光绪与慈禧 , 十九世纪英国诗人阿尔杰农·斯温伯恩与爱德华·菲茨杰拉德 , 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 。
在《土星之环》最后篇幅中 , 塞巴尔德又一次回到小说最初提及的英国作家托马斯·布朗那里 。 毫无疑问 , 正是以上这些在现时时间与湮灭时间穿行的记忆 , 使小说开篇的那个场景得以出现:叙述者完成了对萨福克郡的徒步穿行 , 对旅行的回忆使他“在一种几乎完全不能动弹的状态中被送进郡治诺里奇的医院” 。
推荐阅读
- 新京报评论|“老漂族”难过七夕,背后是一个需要被看见的“沉默群体” | 新京报专栏
- 新京报|两名驴友挑战“瀑降”遇险,景区无需一味追求网红项目
- 新京报|北京民俗博物馆里过七夕,体验投针验巧、凤仙花染指甲
- 新京报|舌尖上的七夕,浪漫也要美食相伴
- 新京报|摩登日记|工艺繁杂的蕾丝,曾是欧洲宫廷的专属
- 新京报|新员工不喝酒被打耳光:面子与权力之下的酒桌“虐”文化
- 新京报|2020款新缤智7月销量同比增179%,将聚焦年轻消费者焕新
- 新京报|好物│特殊的日子,让家居小物为你创造浪漫
- 新京报|贵州滴水滩瀑布两驴友挑战“瀑降”遇险,救援队:正设法救援
- 新京报|七夕节与“三观党”:当代年轻人的爱情观更保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