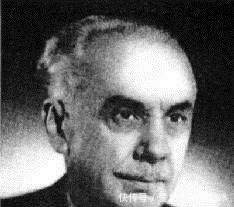以暴制暴 , 暗怀的是玉石俱焚的必死之心 。
许多人以为战争已过 , 恶徒也随之消失 。
但事实上 , 天谴未至 , 反而青云直上 。
就像重磅BOSS金将军 。
身居高位 , 是钱权利兼收的既得者 。
他是战争英雄 , 被国民树立雕像称颂 。
但事实却是 , 金将军才是最大的卖国贼 。
战争期间 , 他利用军职骗取国民信任 。
将青年输送给日军 , 助推侵略暴行 。
谎称为妇女提供工作 , 实则送去慰安 。
甚至协助日军策划改名计划 , 抹去本土文明 。
这样的人来到和平年代 , 血液仍是冰冷的 。
老韩复仇过程中 , 发现杰森处境凄惨 。
杰森的父亲为金将军企业卖命 , 因事故余生只能在轮椅上度日 。
可受害者非但没有得到赔偿 , 反而被当做蝼蚁清扫 。
抗议者冒着严寒等在金将军府邸外 , 求一份合理补偿 。
一墙之隔内 , 却是金碧辉煌的住所和傲慢的眼神 。
无论什么时代 , 恶鬼仍是恶鬼 。
正如片名《我记得》之意 。
老韩的复仇 , 是因他亲历炼狱 , 苦痛深刻心中 。
但一场战争中 , 「老韩」远不止一人 。
所复之仇跨越时代 , 又何尝只是历史遗产 。
近年来 , 韩国电影确实风光无限 。
《寄生虫》横扫奥斯卡 。
《分手的决心》闪耀戛纳 。
在商业性与艺术表达之间 , 韩影不断摸索出平衡之道 。
有人嘲笑 , 有人不屑 。
但不可否认的是 , 韩国电影工业体系的发达与完善 。
但想把流水线产品做出彩 , 套路远远不够 , 仍需另辟蹊径 。
《我记得》改编自2015年加拿大电影《记住》 , 故事发展与人物背景相似 。
最大的不同之处 , 是老者的战争经历 。
原版中 , 是身为犹太人的古特曼向纳粹德军的复仇 。
韩版《我记得》就对这一设定做了本土化调试 。
日军侵占东亚计划是多国的伤痛历史 。
建筑在共同记忆之上的改编 , 增加了观影者的共鸣 。
另一方面 , 抗日虽是「主旋律」题材 。
但在许多韩影中的呈现方式却并不沉重枯燥 。
战争的创伤面再现 , 很多时候是自戕性铭刻 。
对于许多想在电影中休憩片刻的观众而言难以承受 。
正如《一九四二》当年在市场遇冷 , 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观众不愿到影院里「花钱找苦吃」 。
但《我记得》套用爽片模式 , 甚至加入了搞笑桥段 。
通俗化地将「重话轻说」 , 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受众面 。
同时也达到了商业性与内容上的双赢 。
这种轻盈的视角切入 , 《我记得》并非孤例 。
2017年 , 电影《我能说》上映 , 横扫韩国各大电影奖项 。
罗文姬饰演的罗奶奶是个难缠的「上访」专业户 。
邻里琐事 , 路有不平 , 她统统要管 。
跟市政厅公务员的暗暗角力更是笑料百出 。
乍看 , 是一个喜剧故事 。
但随着剧情发展 , 电影的野心也图穷匕见 。
为了再见失散在美国的家人 , 也为了实现好友出国演讲的愿望 。
罗奶奶开始跟公务员民载学习英语 。
嬉笑怒骂中二人成为忘年交 , 也借此揭开了罗奶奶过往的惨痛身世 。
原来 , 罗奶奶13岁时曾被日军抓去慰安 。
受尽非人折磨 , 一度准备结束生命 。
是好友的支撑让她活了下来 , 但家人却以她为耻 , 不愿来往 。
罗奶奶孤身一人 , 无儿无女 , 只剩邻里给予她温暖 。
罗奶奶此番学英语 , 是为了挽回离她而去的家人 。
更是要对国际社会揭发日军当年的恶行 。
在国际演讲台上 , 罗奶奶用身上的伤痕驳斥日方的诡辩 。
用学到的英语铿锵有力地控诉质问 , 场面震撼人心 。
真实事件改编的力度 , 让观众在电影内外都数次泪目 。
但更重要的是 , 如此沉重的历史伤痛却转能化成喜剧 , 足见编排功力 。
除此之外 , 《我记得》中提及的改名运动 , 也被反映在另一部韩国电影中 。
2019年的韩国电影《词典》 , 正是相关背景 。
彼时日占区要求朝鲜人民起日本名、说日语 , 稍有不从便性命堪忧 。
文化洗脑让本民族文明火种奄奄一息 。
在这样的恐怖气氛下 , 护送朝鲜语词典的重任却落在了一个文盲阿金身上 。
推荐阅读
- 「新概念英语」,It's too small,这位女士有点不开心了!
- 许多|看新闻才知道团体解散!盘点8组「被经纪公司欺负」的韩星
- 马斯克秀中文「七步诗」引热议;抖音、飞书「崩」上热搜;雅虎停止在中国大陆服务
- 虞书欣|7点认识「小兰花」虞书欣:偶像是Lisa、现实生活是白富美
- 高速公路「匝道」概念与通行注意事项-全解析 什么是高速公路匝道
- 别误会,日本网友对你说「草」时,其实想表达是一种植物
- 紫米|「医学级护肤品牌」是如何冲击功效护肤新赛道的?
- |蔡允洁怀孕8个月冲动剪短发!被警告「孕妇别拿刀」:又不是我剪
- 音乐银行|新女团打败润荷夺一位「音源、专辑销量却是0分」!《音乐银行》计分又惹议
- 山下智久|《今际2》山下智久「真的全脱」画面曝光!山崎贤人、土屋太凤水中暧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