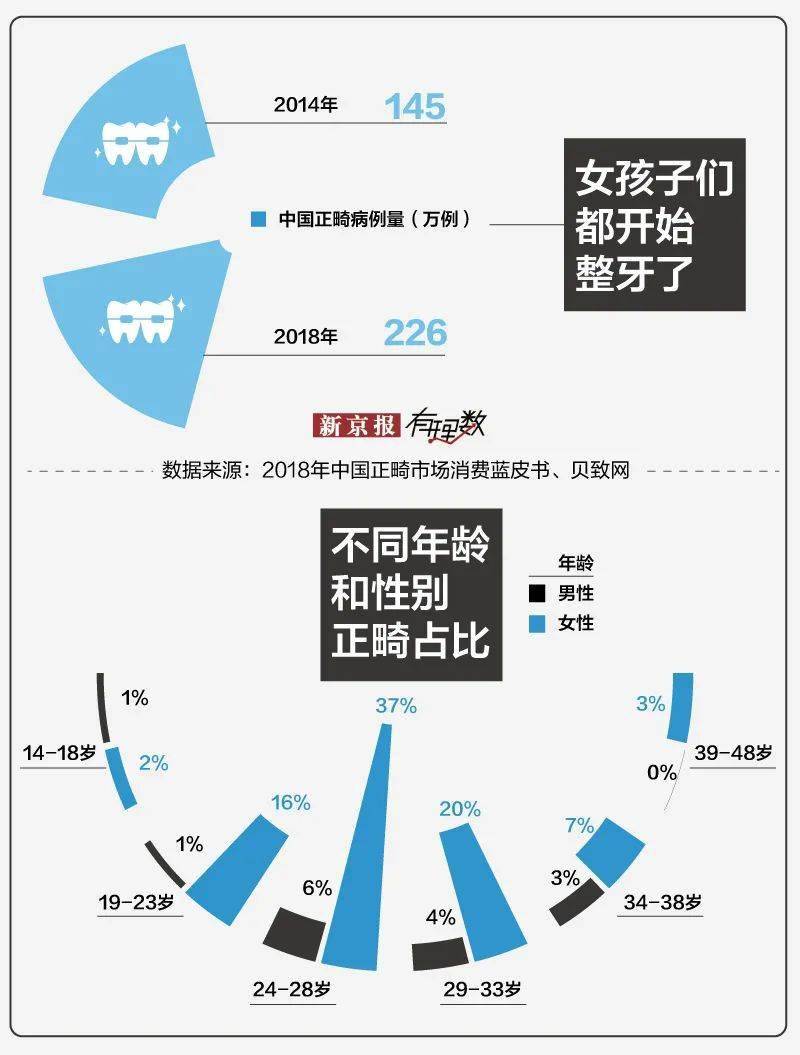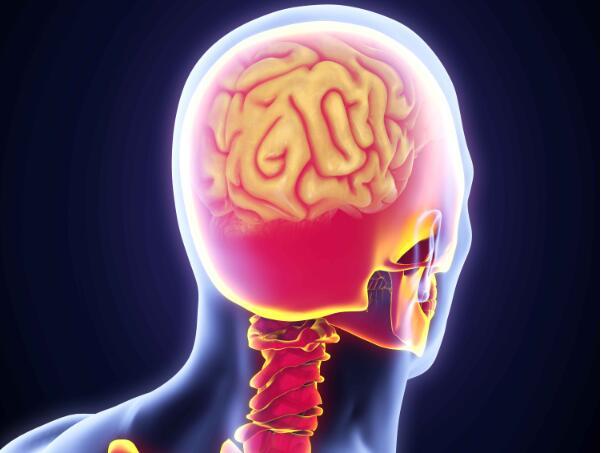最后的匪帮?什么的匪徒
她从门里走出去了,而房间里的一切生命也跟着她出去了 。她把我的人物全带走了 。
——舍伍德·安德森《寂寞》
1
电话再次响起来的时候已是正午,阳光炽热地晒着窗户 。马革一身汗水地猫在窗前,脚下躺着其他两名匪徒的尸体 。他们每人身体里都有一颗子弹,这些子弹证明他们已经是死人 。正在进入酷暑的果城,不久即将对他们做出腐烂的宣告 。
窗外人行便道上空无一人,只有太阳明亮地打在灰绿相间的砖块上 。稍远处的马路上有车辆和人群,但不是马革平时看到的交通工具和行人,而是一些跟他对峙的人 。马革知道,几个小时以来,电视台正在频繁使用对峙这个词——情况一定是这样:他置身其中的这间小超市被作为画面背景,一个主持人手持话筒很激动地宣布:到目前为止,歹徒与警方已对峙X个小时……马革想象着此时此刻,在果城、果城以外的地方、甚至在这个宇宙上,正在上演着多少这样的场景 。他想象不出却敢肯定,至少不是他一个人在孤军奋战 。这样一想,马革的心胸就无限开阔起来 。
马革拿着的电话是超市里的移动座机,它的主人三十多岁的超市老板小黄嘴里塞着布,五花大绑着,被马革再次拉来充当移动盾牌 。电话里换了一个声音,但马革知道,无论跟他谈判的人如何变来变去,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从马革这里骗出所有的人质,然后结果了他 。现在马革手里还有三名人质,一是小黄;二是小黄的老婆;三是一名女医生,先前被派来替换了一名事发时正在超市购物的顾客 。
马革很警惕地听着电话,这回他们换了一个女人,马革从窗户里看向那些跟他对峙的人,却看不到她在哪儿 。喂,你在听吗?那女人喂了一声,又喂了一声 。马革不说话 。他知道,对方能听到他的喘气声 。
我是朱平平 。对方又说 。
马革喉口拥堆着无数的酸楚,他把头靠向窗帘,闭目压制着这突兀的、沉重的哀伤 。他知道此刻他需要的是冷酷和坚硬,而绝非软弱和眼泪 。

文章插图
马革,我是朱平平 。朱平平又说了一句,然后停顿了几秒钟,说,马革,不要抵抗了,出来争取宽大处理 。
这套说辞包含着无穷无尽的欺骗性,把马革的情绪从哀伤中骤然拉出,代之以火焰般升腾而起的愤怒和仇恨 。你来,他对着电话简短地说 。
电话那头出现短暂的停顿,什么声音也没有 。几秒钟之后,朱平平转述了警方的话,为那短暂的寂静做了说明:我可以去,但有个条件,释放里面的人质 。马革不容置疑地用四个字表明在这场对峙中他才是主导位置上的人:只放一个!
又是沉默 。几秒钟后朱平平答复道:可以 。
马革放下电话,回头看被他掌握命运的三个人质 。嘴里塞着一团布的小黄脸色蜡黄地缩在窗下,蓝色大短裤洇着几团尿湿的痕迹;小黄老婆瘫坐在几个酸奶箱子后面,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 。几个小时前,正是这女人偷偷打电话报的警;相较这两个吓坏的人,女医生由于看多了死人,还显得镇定一些 。女医生被马革叫来,是为了救中弹的灰灰和小瓦 。其实,女医生来后看到的已经是尸体 。
这三名人质里,唯一让马革感到有点对不住的就是女医生 。他说,待会儿来人之后,你就可以走了 。女医生看看马革的腰部,说,要不先让别人走吧,你受伤了 。
马革感到腰上又一阵火辣辣的疼 。在之前的那场对垒中,警方派来的狙击手先后射中灰灰和小瓦,射他的那粒子弹则只穿透他右腰的脂肪层 。在那之后他以眼还眼,射死一个趁乱打算用一只板凳将他砸晕的顾客 。他的这一暴力行为像一声断喝,止住了那些自以为是的狙击手 。没被狙击手一枪毙命并不是马革的运气,相反,从那之后他一直耿耿于怀,觉得那伤口辱没了自己曾经是一名越战老兵的荣誉 。
此刻,在这间超市,马革竟然奇怪地想起老山前线的猫耳洞 。钻在猫耳洞里的那一年他才只有十七岁,比灰灰还要小两岁 。他看了看灰灰,这十九岁的孩子由于死前的疼痛,眉头拧成几道深深的皱褶 。马革瞬间改变了主意,他拿起电话摁重拨键,对那边接电话的一个警察简短地说,计划改变了 。
穿过窗户,马革看到已经离开对面那群人的朱平平在马路中间停了下来,犹疑不定地站在绿化带里 。她刚要穿过的那片绿化带开满月季,其中有一丛是白色的,跟超市一只花瓶里插着的那朵一样 。朱平平就站在那丛白月季旁边,朝他这边努力地看 。他拿着电话,花两分钟时间回忆了一下,然后说,让她回去,先叫陈胜利来,住香槟小区 。
推荐阅读
- 警察|国考中最受欢迎的5大系统,待遇发展都很好,报名人数逐年增加
- 何家劲|和影帝同居8年,后又被何家劲独宠3年,最后转身就嫁入豪门
- 周杰伦|每次周杰伦出新专辑,新专辑最初带来的反馈,都是「江郎才尽」!
- 我们在教育孩子方面欠缺的?孩子最欠缺的是什么
- 祝绪丹|人美戏好祝绪丹,最美周芷若,嘉行的眼光没错
- 副作用最小的抗癫药物
- 汤唯|很有韵味的文艺片女星!汤唯成春史电影奖最佳女主角,春夏有气质
- 淦天雷|《黑白禁区》苏灵没等到最爱的春天,淦天雷也没有娶到最爱的姑娘
- 刘恺威|《披哥2》三公:郝云点亮舞台被淘汰,到哪拆哪的刘恺威笑到最后
- 史上最快燃脂运动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