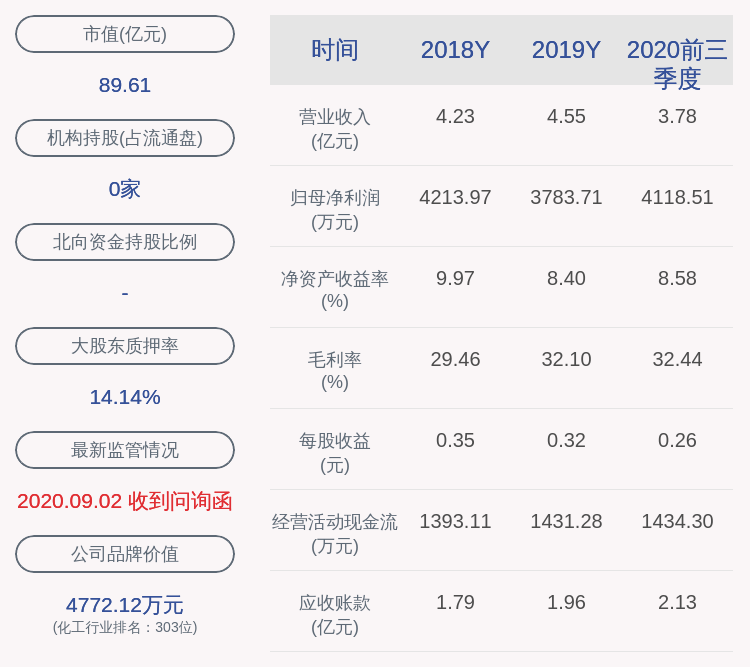йҳҝжіўзҪ—|д»Җд№ҲжҜ”жҲ‘们жӣҙдәҶи§ЈиҮӘе·ұпјҡгҖҠжҲ‘зҡ„жңӢеҸӢйҳҝжіўзҪ—гҖӢ( дәҢ )
гҖҗ йҳҝжіўзҪ—|д»Җд№ҲжҜ”жҲ‘们жӣҙдәҶи§ЈиҮӘе·ұпјҡгҖҠжҲ‘зҡ„жңӢеҸӢйҳҝжіўзҪ—гҖӢгҖ‘ж•ҙйғЁе°ҸиҜҙйғҪжҳҜеӯӨзӢ¬зҡ„е‘“иҜӯпјҢжҳҜдёҺжӯ»иҖ…зҡ„и°ҲеҝғпјҢд»ҘдёҖдёӘжңӢеҸӢгҖҒеҜјеёҲе’ҢжҒӢдәәзҡ„жӯ»дәЎејҖе§ӢпјҢд»ҘдёҖеҸӘжё©жҡ–дәәеҝғзҡ„зӢ—зҡ„жӯ»дәЎз»“жқҹгҖӮ
иҝҷж ·зҡ„и®ҫзҪ®пјҢзӯүдәҺеңЁиҖғйӘҢдҪңиҖ…зңҹиҜҡзҡ„жһҒйҷҗгҖӮеҸӘиҰҒжңүдёҖзӮ№зӮ№жІ№ж»‘пјҢдёҖзӮ№зӮ№еӨёеј зҡ„жҲҸеү§жҖ§пјҢе°ұдјҡжҜҒдәҶиҝҷйғЁдҪңе“ҒгҖӮдҪ еҝ…йЎ»е§Ӣз»ҲжІүжөёеңЁйӮЈд»ҪжӮІз—ӣд№ӢдёӯгҖӮдҪ дёҚиғҪжүӢиҲһи¶іи№Ҳең°и®Іж•…дәӢпјҢдёҚиғҪжңүеӨҙжңүе°ҫең°жёІжҹ“жғ…иҠӮпјҢдёҚиғҪеҶ·йқҷе®ўи§Ӯең°зҪ®иә«дәӢеӨ–гҖӮдҪ з”ҡиҮідёҚиғҪжҡҙйңІдёҖдёҒзӮ№зҡ„иЁҖдёҚз”ұиЎ·гҖӮиҝҷжң¬е°ҸиҜҙ并没жңүиҝҪжұӮд»Җд№Ҳе®һйӘҢжҖ§пјҢе®ғд№ӢжүҖд»Ҙзү№еҲ«пјҢд№ӢжүҖд»ҘдёҚеҗҢдәҺдёҖиҲ¬ж„Ҹд№үдёҠзҡ„е°ҸиҜҙпјҢеҸӘжҳҜеӣ дёәе®ғеҝ…йЎ»е°ҠйҮҚиҝҷд»ҪзңҹиҜҡе’Ңжғ…ж„ҹгҖӮ
еҠӘж¶…ж–ҜеҒҡеҲ°дәҶиҝҷдёҖзӮ№пјҢеҮӯеҖҹеҘ№еҜ№иҮӘжҲ‘е®үж…°е’ҢеӨҡж„Ғе–„ж„ҹзҡ„иӯҰжғ•пјҢеҘ№еҶҷеҮәдәҶдёҖз§Қзңҹе®һзҡ„гҖҒеҠЁдәәзҡ„ж„ҹи§ҰгҖӮ
еҗҢдёәеҶҷдҪңж•ҷеӯҰиҖ…зҡ„иҮӘжҲ‘иҙЁз–‘
дҪңдёәиҜ»иҖ…пјҢжҲ‘е’ҢеҠӘж¶…ж–Ҝжң¬дәәдёҖж ·пјҢи·ҹд№ҰдёӯйӮЈдҪҚеҸҷдәӢиҖ…пјҢд»ҘеҸҠйӮЈдҪҚжӯ»еҺ»зҡ„дҪң家йғҪжңүзқҖзӣёеҗҢзҡ„иҒҢдёҡпјҢйғҪеңЁеӨ§еӯҰйҮҢж•ҷеҶҷдҪңиҜҫгҖӮжӣҙе·§еҗҲзҡ„жҳҜпјҢжҲ‘е’Ң他们жӢҘжңүе…ұеҗҢзҡ„ж–ҮеӯҰеҒ¶еғҸJ.M.еә“еҲҮпјҢдёҖдёӘеҶ·еі»зҡ„жҖҖз–‘дё»д№үиҖ…гҖӮ

ж–Үз« жҸ’еӣҫ
иҘҝж јдёҪеҫ·В·еҠӘж¶…ж–ҜпјҲSigrid Nunezпјү
еҸҜжғіиҖҢзҹҘпјҢжҲ‘еҜ№иҝҷйғЁе°ҸиҜҙжңүзқҖи¶…еҮәдёҖиҲ¬иҜ»иҖ…зҡ„ејәзғҲе…ұйёЈгҖӮжҲ‘ж·ұзҹҘд№Ұдёӯеұ•зҺ°зҡ„йӮЈз§Қж— еҘҲпјҡжӣҫз»ҸжҢҮеј•жҲ‘们иө°дёҠж–ҮеӯҰе’ҢеҶҷдҪңд№Ӣи·Ҝзҡ„еҘүзҢ®зІҫзҘһе’Ңиҷ”иҜҡеҝғжҖҒпјҢеҰӮд»ҠжҲҗдәҶиҗҪеҗҺдәҺж—¶д»Јзҡ„ж ҮзӯҫгҖӮжҲ‘们ејҖеҮәзҡ„д№ҰеҚ•пјҢжҖ»жҳҜеҸ—еҲ°е№ҙиҪ»дәәзҡ„й„ҷеӨ·гҖӮйӮЈдәӣжүҖи°“зҡ„ж–Ү科尖еӯҗз”ҹж №жң¬дёҚжҮӮж–Үеӯ—зҡ„еҘҪеқҸпјҢиҖҢдё”жҜ«дёҚеңЁж„Ҹж ҮзӮ№з¬ҰеҸ·зҡ„дҪҚзҪ®гҖӮеӯҰз”ҹ们жүҫеҗ„з§ҚеҖҹеҸЈйҖғйҒҝйҳ…иҜ»дҪңдёҡгҖӮеӨ§еӯҰж Ўеӣӯе·Із»ҸзҰ»ж–ҮеӯҰйӮЈд№ҲиҝңпјҢд»ҘиҮідәҺжҲ‘们дёҚзҹҘйҒ“еҰӮдҪ•е®үзҪ®иҮӘе·ұзҡ„зҗҶжғіпјҢе®үзҪ®жҲ‘们еҝғдёӯзҡ„зҘһжҳҺгҖӮ
д№ҰдёӯеҸ‘еҮәдәҶеӨӘеӨҡжҲ‘жғіеҸ‘зҡ„зүўйӘҡпјҡ
еҰӮд»ҠжҜҸдёӘдәәйғҪеҶҷдҪңпјҢе°ұеҰӮеҗҢжҜҸдёӘдәәйғҪжҺ’дҫҝдёҖж ·пјӣдёҖеҗ¬еҲ°еӨ©иөӢиҝҷдёӘиҜҚпјҢеҫҲеӨҡдәәе°ұжғідјёжүӢеҺ»жӢҝжһӘгҖӮ
еҠ йҮҢжЈ®В·еҹәеӢ’жҳҜеҜ№зҡ„пјҢдҪ иҜҙпјҢеҪ“дәәдәәйғҪжҳҜдҪң家зҡ„ж—¶еҖҷпјҢе°ұжІЎдәәжҳҜдҪң家дәҶгҖӮ
дҪ дёҚеҶҚзӣёдҝЎе°ҸиҜҙзҡ„ж„Ҹд№үвҖ”вҖ”иҖҢд»ҠпјҢдёҖйғЁе°ҸиҜҙдёҚз®ЎеҶҷеҫ—еӨҡд№ҲзІҫеҪ©пјҢдёҚз®Ўе…¶жҖқжғіеӨҡд№Ҳдё°еҜҢпјҢйғҪдёҚдјҡеҜ№зӨҫдјҡдә§з”ҹд»»дҪ•з§ҜжһҒеҪұе“ҚгҖӮ
жҲ‘еңЁж•ҷд№Ұж—¶жіЁж„ҸеҲ°пјҢжҜҸдёҖе№ҙжҲ‘зҡ„еӯҰз”ҹеҜ№дҪң家зҡ„иҜ„д»·дјјд№ҺйғҪиҰҒйҷҚдҪҺдёҖзӮ№зӮ№гҖӮдҪҶжҳҜпјҢеҪ“йӮЈдәӣжғіжҲҗдёәдҪң家зҡ„дәәд»Ҙж¶ҲжһҒзҡ„зңје…үзңӢеҫ…дҪң家зҡ„ж—¶еҖҷпјҢиҝҷеҸҲж„Ҹе‘ізқҖд»Җд№Ҳе‘ўпјҹдҪ иғҪжғіиұЎдёҖдёӘеӯҰиҲһи№Ҳзҡ„еӯҰз”ҹеҜ№зәҪзәҰеёӮиҠӯи•ҫиҲһеӣўжңүиҝҷз§Қж„ҹи§үеҗ—пјҹжҲ–иҖ…е№ҙиҪ»иҝҗеҠЁе‘ҳй„ҷи§ҶеҘҘиҝҗеҶ еҶӣе‘ўпјҹ
зүўйӘҡеҪ’зүўйӘҡпјҢвҖңжҲ‘вҖқиҷҪ然еҜ№ж–ҮеӯҰзҡ„еӨ„еўғдёҚжҠұеёҢжңӣпјҢеҗҢж—¶еҚҙеҸҲжҖҖзқҖжңҹеҫ…еҺ»еҸӮдёҺеҗ„з§ҚеҶҷдҪңйЎ№зӣ®пјҢдёәжІ»з–—дёӯеҝғйӮЈдәӣеҸ—иҝҮеҲӣдјӨзҡ„еҘіжҖ§дёҠеҶҷдҪңиҜҫпјҢжңҹжңӣеҶҷдҪңиғҪеӨҹеё®еҠ©еҘ№д»¬жҺ’йҒЈеҷ©жўҰгҖӮиҝҷжң¬иә«иҜҒжҳҺдәҶеҜ№еҶҷдҪңжҖҖжңүзҡ„дҝЎеҝөгҖӮ
иҘҝж јдёҪеҫ·?еҠӘж¶…ж–ҜдёҺж ЎеҸӢStephen Kuusisto
然иҖҢпјҢеҶҷдҪңиҝҷдёӘиЎҢдёәпјҢд№ҹи®ёд»Һж №жң¬дёҠи®ІпјҢжіЁе®ҡж— жі•иҮӘ然ең°иһҚе…Ҙе…¬е…ұиҜӯеўғд№ӢдёӯгҖӮдёҚжҳҜж—¶д»Је’ҢзӨҫдјҡзҡ„й—®йўҳпјҢиҖҢжҳҜеҶҷдҪңжң¬иә«зҡ„й—®йўҳгҖӮеҰӮжһңе®ғжҳҜзңҹиҜҡзҡ„пјҢе°ұеҝ…然еёҰжңүдёҖз§Қз§ҒеҜҶжҖ§пјҢдёҖз§Қдҫөз•ҘжҖ§пјҢдёҖз§ҚдёҚйҒ“еҫ·зҡ„ж„Ҹе‘ігҖӮд№ҰдёӯеҶҷйҒ“пјҡ
ж— и®әе“Әж¬ЎжҲ‘еҺ»еҸӮеҠ иҜ»д№Ұжҙ»еҠЁпјҢжҲ‘йғҪеҝҚдёҚдҪҸдёәдҪңиҖ…ж„ҹеҲ°е°ҙе°¬гҖӮжҲ‘дјҡй—®иҮӘе·ұпјҢжҲ‘еёҢжңӣеҸ°дёҠзҡ„йӮЈдёӘдәәжҳҜжҲ‘еҗ—пјҹзңҹе®һзҡ„еӣһзӯ”жҳҜпјҢз»қеҜ№дёҚеёҢжңӣгҖӮиҖҢдё”дёҚд»…д»…жҳҜжҲ‘гҖӮдҪ еҸҜд»Ҙж„ҹи§үеҲ°е…¶д»–зҡ„еҗ¬дј—пјҢд№ҹжҳҜеҗҢж ·зҡ„дёҚиҮӘеңЁгҖӮ
еҶҷдҪңжң¬иә«е·Із»Ҹи¶іеӨҹзҹӣзӣҫе’Ңе°ҙе°¬дәҶпјҢжӣҙдҪ•еҶөжҳҜж•ҷеҶҷдҪңе‘ўпјҹеҠӘж¶…ж–ҜжҸҗеҲ°пјҢеӯҰз”ҹ们з»ҸеёёжҸҗеҮәиҙЁз–‘пјҢи®ӨдёәйҮҢе°”е…Ӣиҝҷж ·зҡ„дҪң家声称еҶҷдҪңйңҖиҰҒзү§еёҲиҲ¬зҡ„еҘүзҢ®пјҢиҜ•еӣҫе°ҶеҶҷдҪңеҪ“жҲҗдёҖз§Қе®—ж•ҷпјҢиҝҷз§Қи§ӮзӮ№жҳҜиҚ’и°¬зҡ„гҖӮ他们жҢҮиҙЈйӮЈдәӣз»Ҹе…ёдҪңе“ҒжҳҜж„ҸиҜҶеҪўжҖҒзҡ„з»“жҷ¶пјҢ他们ж„ҹи§үдёҚеҲ°йӮЈдәӣдҪңе“ҒжҳҜеңЁеҜ№д»–们иҜҙиҜқгҖӮ他们и®ӨдёәпјҢеұһдәҺз»Ҹе…ёдҪң家们зҡ„дё–з•Ңе·Із»Ҹж¶ҲеӨұдәҶгҖӮ
жҲ‘зҹҘйҒ“еҘ№иҜҙзҡ„йғҪжҳҜзңҹзҡ„гҖӮеӣ дёәжҲ‘жҜҸеӨ©йғҪеңЁдҪ“йӘҢиҝҷдёҖеҲҮгҖӮжҳҜе•ҠпјҢж–ҮеӯҰжӯЈеңЁж¶ҲдәЎпјҢжҲ‘们иҝҷдәӣж•ҷеҶҷдҪңзҡ„дәәпјҢдёҚжӯЈеғҸйІҒиҝ…笔дёӢзҡ„еӯ”д№ҷе·ұдёҖж ·еҗ—пјҢеёҰзқҖж»‘зЁҪзҡ„дјҳи¶Ҡж„ҹпјҢд»ҘжҮӮеҫ—иҢҙеӯ—зҡ„еӣӣж ·еҶҷжі•иҖҢеҫ—ж„ҸпјҢе®һйҷ…дёҠеҚҙе·Іиў«ж—¶д»Јиҫ—иҪ§иҖҢиҝҮпјҢиҝңиҝңз”©еңЁиә«еҗҺгҖӮ
然иҖҢпјҢд»Һж №жң¬дёҠи®ІпјҢжҲ‘们иҝҳжңүдёҖжқЎеә•зәҝгҖӮйӮЈе°ұжҳҜжҲ‘们иө·з ҒзӣёдҝЎеҶҷдҪңд№ӢдәҺжҲ‘们дёӘдәәзҡ„ж„Ҹд№үгҖӮиҝҷжҳҜжңҖеҗҺзҡ„е Ўеһ’гҖӮд№ҹи®ёжҳҜеҮәдәҺеҜ№иҝҷеә§е Ўеһ’зҡ„жҚҚеҚ«пјҢеҠӘж¶…ж–ҜеңЁж•ҙжң¬е°ҸиҜҙдёӯдёҖйЎ№дёҖйЎ№ең°еҝ е®һи·өиЎҢеҘ№еңЁеҶҷдҪңиҜҫдёҠзҡ„е»әи®®пјҢеғҸзҺ°иә«иҜҙжі•пјҢе‘ҠиҜүжҜҸдёҖдёӘиҜ»иҖ…пјҢеҶҷдҪңжҳҜеҰӮдҪ•жү“ејҖдёҖдёӘдәәзҡ„еҶ…еҝғпјҢ并з»ҷдәҲз–—жІ»пјҡдёҺе…¶еҶҷдҪ зҹҘйҒ“зҡ„дёңиҘҝпјҢдёҚеҰӮеҶҷдҪ зңӢеҲ°зҡ„дёңиҘҝпјӣиЎЁиҫҫдёҖдәӣй•ҝд№…д»ҘжқҘеҶ…еҝғж·ұеӨ„зҡ„ж„ҹи§ҰпјӣеҶҷз§ҒеҜҶзҡ„ж—Ҙи®°пјӣеҶҷдёҖеҶҷзҺ°еңЁжҲ–иҝҮеҺ»еҜ№дҪ еҫҲйҮҚиҰҒзҡ„д»»дҪ•дёңиҘҝпјӣжҠҠдҪ ж— жі•йқўеҜ№зҡ„зңҹе®һиҜүиҜёжғіиұЎеҠӣпјӣжү“иҙҘз©әзҷҪйЎөвҖҰвҖҰ
жҺЁиҚҗйҳ…иҜ»
- йӯ”йҒ“зҘ–еёҲдёӯпјҢеӨ§е®¶жңҖжҖ•еҗ¬еҲ°д»Җд№ҲпјҹзңӢеҲ°з¬¬дёүеҸҘе·Із»ҸеҝҚдёҚдҪҸе“ӯдәҶ
- жҳҺжңқжң«е№ҙиө„жң¬дё»д№үз»ҸжөҺе’ҢжҖқжғіеҸ‘еұ•еҲ°дәҶд»Җд№ҲзЁӢеәҰпјҢеҪ“ж—¶зҡ„з»ҹжІ»йҳ¶зә§жҳҜеҗҰе·Із»Ҹж„ҸиҜҶеҲ°дәҶиҝҷдёӘй—®йўҳпјҹ
- зәўжҘјжўҰйҮҢпјҢиҙҫзҗҸдёәд»Җд№ҲиҖҒе–ңж¬ўең°дҪҚдҪҺдёӢзҡ„еҘідәәиҝҷж ·еҲҶжһҗдҪ еҸҜиөһеҗҢ
- еҰӮдҪ•зӣҙи§Ӯең°иҜҙжҳҺжұүжңқеҲ°еә•жңүеӨҡејәеӨ§пјҹ
- иў«дё»дәәеёҰиө°зҡ„еҰ–жҖӘдјҡжҳҜд»Җд№ҲдёӢеңәжңҖжғЁзҡ„иҺ«иҝҮдәҺиҝҷеҸӘеҰ–жҖӘ
- е°ҒзҘһжҰңдёүдҪҚеңЈдәәзҡ„е®һеҠӣйӮЈдёӘжңҖејәпјҢдёәд»Җд№Ҳе…ғе§ӢеӨ©е°ҠжҲҗдёәжңҖеҗҺзҡ„иөўе®¶пјҹ
- зҪ—зҙ пјҡеҜ№е№іеәёзҡ„еҙҮжӢңжҳҜжҲ‘们иҝҷдёӘж—¶д»ЈжңҖеӨ§зҡ„жҒ¶д№ӢдёҖ
- дёӯеӣҪжӯҰжңҜз”ұжқҘе·Ід№…пјҢвҖңжӯҰеӯҰзӣӣдё–вҖқе’ҢвҖңжӯҰеӯҰжң«дё–вҖқеҲҶеҲ«жҳҜд»Җд№Ҳж—¶еҖҷпјҹ
- и’Ӣд»Ӣзҹі4дёӘвҖңжҠҠе…„ејҹвҖқзҡ„д№Ұжі•пјҢжӮЁдјҡз»ҷеҮәд»Җд№ҲиҜ„д»·пјҹ
- иҘҝжёёи®°пјҢдёәд»Җд№ҲеӯҷжӮҹз©әж—©е°ұзҹҘйҒ“пјҢд»–е·Із»ҸйЈһеҮәдәҶеҰӮжқҘдҪӣзҘ–зҡ„жүӢжҺҢеҝғ






![[延иҝҹйҖҖдј‘е№ҙйҫ„]延иҝҹйҖҖдј‘еҮәж–°еҠЁжҖҒпјҢи·ҹжҜҸдёӘдәәйғҪжҒҜжҒҜзӣёе…іпјҢзҺ°еңЁзҹҘ](/renwen/images/defaultpic.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