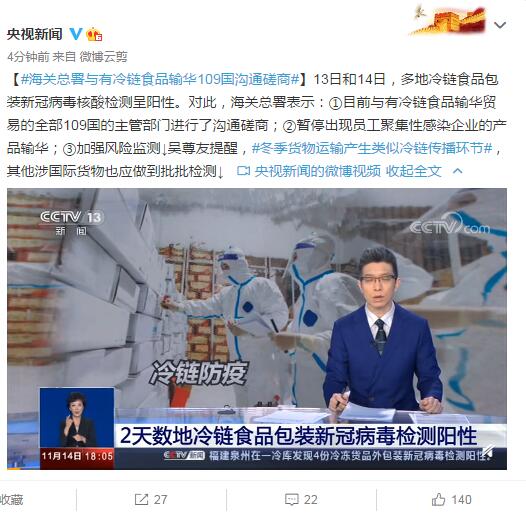艾伟补充道,1980年代的文学是被及时命名的,历史的方向是清晰的,内在的文学逻辑是启蒙。但1990年代的文学一直以来只有一个命名——文学的碎片化。
“李洱和我谈起过这个问题,认为文学界需要对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进行重新命名、阐释和评价。即使了到新世纪,文学的内在逻辑依旧是1990年代以来的逻辑,没有改变。”
如何判断“我们是一代人”?
其实,以出生年代为标准划分作家——“60后”“70后”“80后”……这话题已经谈了好多年了。亦有人认为作家根本不需要代际划分,只要有“好作家”与“不好的作家”,或者“活着的作家”与“去世的作家”。
“但我个人认为,中国还是存在代际的问题。”艾伟说,“一方面,因为中国变化太过迅捷,每一代人的生命经验各不相同,由此产生代际。另外一方面,我们根本的历史意志没有改变,我们依旧还是同一代人。”
在他看来,“60后”作家在某种程度上是幸运的,他们有一个完整的中国经验。“我们经历了两个时代,一个我叫它‘革命的年代’,一个我叫它‘经济的年代’。这两个年代表面上看来是截然相反的:一个是禁欲的,一个是纵欲的;一个严肃的,一个戏谑的;一个有所谓的‘信仰’,一个则精神世界完全破败。这两个年代看上去如此不同,但它们背后的逻辑其实是一模一样的,都是革命意识形态的产物,只是互为倒影而已。所以从更大的历史去看,‘60后’‘70后’或‘80后’也好,我们在同一历史意志之中,是同一代人。”
在石一枫看来,比起出生年份,用历史大事件来划分代际或许更为有效:改革开放前后可以说是两个代际,南巡讲话前后可以说是两个代际,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也可以是两个代际,甚至于对整个世界而言,新冠肺炎发生前后都是两个代际。
而路内认为,作家认为的一代人和普罗大众认为的一代人其实是有偏差的,这里有地域政治、精英分子视角等种种因素。技术也同样影响了代际感受,比如出生于1973年的他和一批“80后”作家几乎同时开始使用电脑和互联网,因此也有共同语言。
此外,他能从一些摇滚歌手和电视编剧身上清晰地辨识出“我们是一代人”,这份感觉在一些同龄写作者那里反而是没有的。“所以在泛文化层面上,我们前面说到的同一代人就已经有了‘我者’和‘他者’。”
对作家而言,“经典化”为什么是一个伪命题?
谈及“文学经典化”,在场许多作家都认为它对写作者而言是一个虚无的概念。路内直言“文学经典化”在今天极其难谈:“什么是文学经典化的标准?是获得了文学奖,还是年销一百万册,还是成为‘作家中的作家’?这三个标准没法被一起讨论,它们完全不在一个维度上。如果要有界定,也应该是由评论家来做。”
阿乙也说,写作者往往不确定自己的作品会驶向何方。一部作品从诞生到发表,其实是由文学杂志、评论家、出版社完成它最后的塑形。有的写作者年轻有为,一开始有一二佳作,但缺了有耐心的编辑和评论家的持续关注,不久后也“销声匿迹”。
“我相信每一代都会出现经典作品与作家。但我想,能不能成为经典,这不只是人力的问题,还有天命。你能达到哪一步,这是天命。”孙频说。
付秀莹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经典化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化的概念,而且也是一个当代化的过程,需要当代读者积极参与和认真实践。“我们的读者包括评论界对当代作品的不断筛选、淘洗和逐渐确认,就是一个披沙拣金的过程,是当代文学经典化过程的一部分。任何一个普通的无名的读者,都拥有为我们的作品指认和命名的权利。”
石一枫还提到一个问题——我们说的经典化究竟是文学意义上的经典,还是社会或者政治层面的经典?比如《伤痕》《班主任》是政治学上的经典,《平凡的世界》是社会学上的经典。不只中国,整个世界文学环境中也存在这个问题,《第二十二条军规》《战争与和平》等作品其实是政治学上的经典。
推荐阅读
- “蓉漂”三部曲,“不惑”人生路
- 在杨过和小龙女的爱情之间,到底有着多少道坎?共七道
- 从穷到奢只在一念之间,聊聊汉代清明简朴之风的形成及发展
- 因为李秋水,段誉和虚竹其实还是亲戚!他们之间的关系不简单!
- 玉雕师之间的差距都在这了!
- 方寸之间展牛气 86岁老邮迷准备圆了自己多年的梦
- 两位好汉上梁山,晁盖这样安排,公开了他和宋江之间的矛盾
- 广平二中,老师之间的比赛,有你认识的老师吗?
- 梁山有个派系都是亲戚 但他们之间的关系连狄仁杰也未必能分清!
- 晚清时期,大宗交易使用银两、银元,它们之间有何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