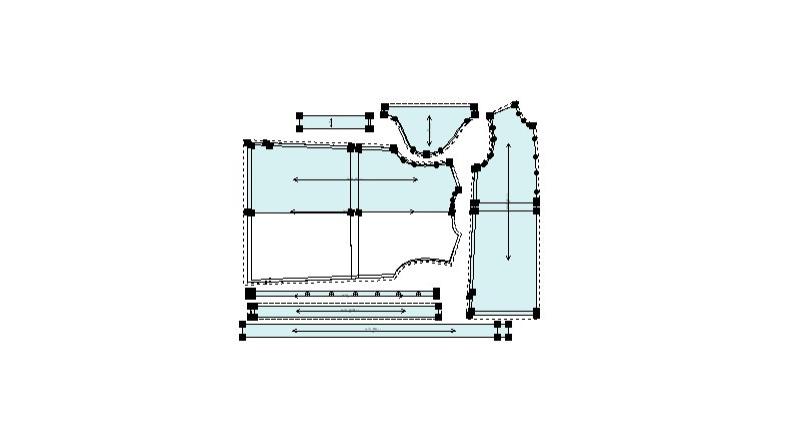几年来,白桦坚持服药,身体状况稳定,也乐观生活,存下了一百多万张旅行时拍的照片。
每一年,他都有两个月的时间在路上。
经验像雪球般积累,工作多年后,我升为护士长,负责告知患者HIV检测结果,跟踪病情。
挂号实名制实施后,我意外发现,许多感染者先前用的都是假名。
这出于不得已的自我保护。歧视像影子般,跟在HIV感染者身后,将这个病与乱性、道德败坏划等号。
一天,一个三十出头的男性,进了我的办公室,沉声说:“我来取结果。”我回复“请坐”,就开始核对他的身份证信息。
一瞥之下,男人帅气、斯文,像精英,我稍微放宽了心。按以往的经验,教育程度高的,对病情的接受度相对高。
HIV感染像身心的双重地震,比病情更难消化的,是它带来的病耻感,许多感染者觉得,自己像在人群里流浪,再也回不到正常的生活轨道。
这名患者叫张钦,检查单上写着“阳性”。
我抬起头,把报告递给了他。张钦盯着那张纸,我开始详细讲解治疗的注意事项。过了半天,却发现他一动不动。
“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我问,像对着墙说话。张钦没有反应。
我忙问:“你父母、亲戚都知道这件事吗?”他沉默。我接下来宽慰的话,也像进了黑洞。第二次的交流,张钦同样封闭了内心。
我有些焦急,担心张钦过不了心里的坎。
曾经有个感染者,甚至打电话给警察说:“我有罪,你抓我走吧。”为与“悲惨的生活”划清界限,还有人会想到自杀。
到第三次见面,张钦意外开口了:“我已经想好怎么去死。”听见这句黑暗的话,我反而松了一口气,他的心门打开了一点点。
我马上顺着问:“你想怎么做?”张钦说:“在天台上,一闭眼往下跳。”他接着告诉我,天台在四层。
和这样的感染者沟通,像站在悬崖边,每句话都是条绳子。
前几次的安抚不管用,我决定改变方式:“从四楼跳,你说你摔残或者摔花了,不更难受吗?你们家几个孩子?”
张钦低声说:“就我。”
“就你一个孩子,那你父母怎么办?你走就走了,你说他们还能活吗?”
我了解到,张钦从小是学霸,成长一路顺风,工作体面。像穿着白衬衫,被泼了一盆墨水,他害怕别人会看见“污点”。
事实上,感染者的隐私受法律保护。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未经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肖像、病史资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其具体身份的信息。
张钦担心:“这段时间没去上班,工作可能保不住了。”我安慰他,可以休整一段再找。只要调整好心态、保护好自己,仍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
由于药盒上有艾滋病的字眼,我教张钦,把药倒进装维生素或鱼油的瓶子,达到掩护的目的。医院的门诊大厅,摆着两个空纸箱,就是用于接收丢掉的药盒。
偶尔外出社交,需要服药的时候,可以去卫生间,把药含在嘴里,回来后再不经意地拿起杯子,用水吞药。
没有陌生人会发现。心态调整后,张钦很快找到新工作,受领导重视,承接了两个大项目,还到国外出差。
人来人往,张钦的面孔逐渐淡出了记忆,我和他也没有特意联系,对于HIV感染者和医护人员来说,没有联系,某种程度上就是最好的状态。
“咚咚咚。”一个下午,敲门声又响了起来,我回答“请进”。门开后,一个帅气的男人探身进来,没想到是张钦。
“前几次过来,看您都在忙,就没进来。还有一次您不在办公室,今天终于碰见了。”他笑着说,“没什么事,就是想您看看我现在状态,是不是特别好?”
我也笑了:“不光特别好,还比以前好,更帅了!”能主动来聊天、分享生活,可见张钦已经走出了疾病的阴影,生活重回正轨,我衷心为他高兴。
医院门诊每天开放300到400个号,长年累月,我接触过成百上千的HIV感染者。
推荐阅读
- 晚年|历史上第一个患“艾滋病”的明星,晚年的做法令世人敬佩!
- 肝吸虫、肺吸虫…感染的孩子才1岁!这个坏习惯很多家庭都有
- 肝吸虫、肺吸虫…感染的孩子才1岁!警惕!这个坏习惯很多家庭都有
- 警惕!1岁男童感染肝吸虫,这个坏习惯很多家庭都有
- 尖锐湿疣|【关注】除了宫颈癌,感染HPV还会导致这种疾病
- 通淋|锅巴菜,见过吗?利尿通淋,清热解毒。治尿路感染和结石
- 中国艾滋病预防阻断机构在深成立,将协助建立HIV阻断体系
- 新冠|视频|能够预防新冠病毒感染的香囊
- 巨噬细胞|肺结核钙化了才能放心,否则有复发的风险,有钙化就感染过结核吗
- 治疗|HIV,如何才能不感染?一旦感染该怎么办?专家倡导早发现早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