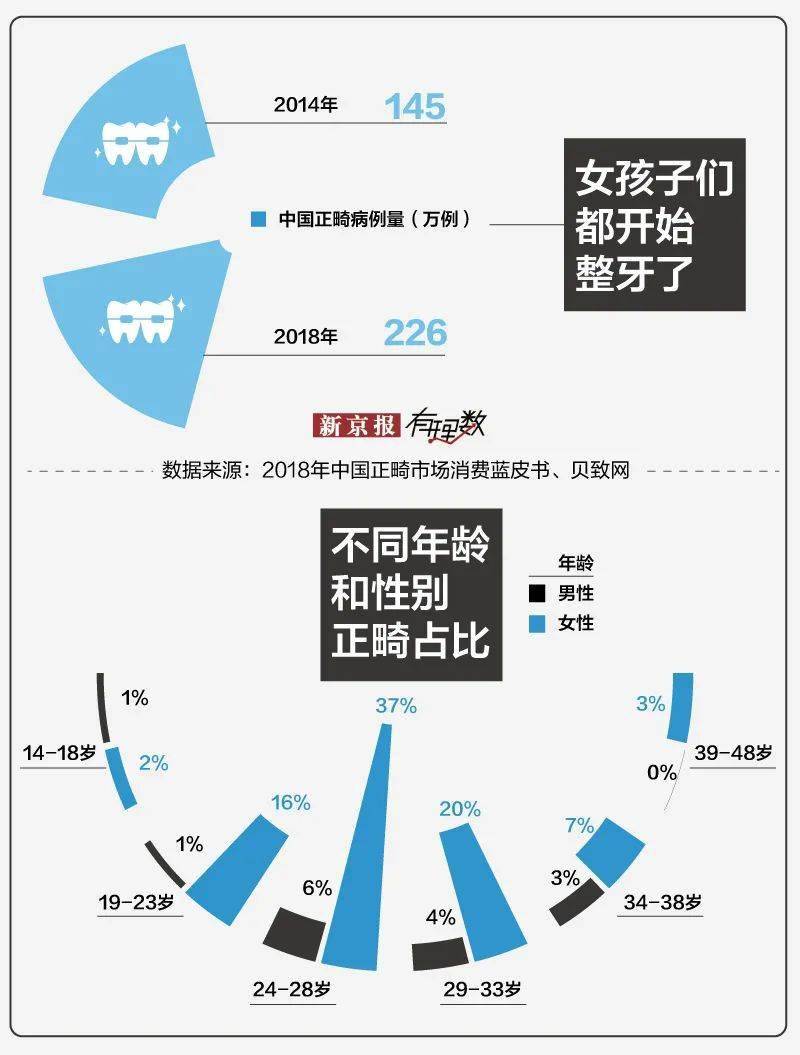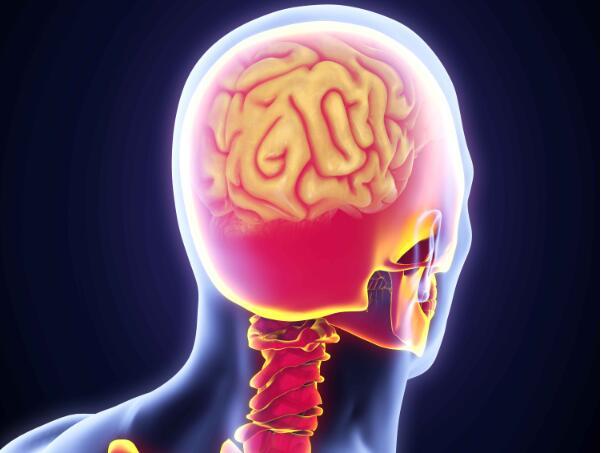зҷҪиңЎж ‘|зҲ¶дәІж ҪдёӢзҡ„зҷҪиңЎж ‘
жң¬ж–ҮеӣҫзүҮ
зҲ¶дәІж ҪдёӢзҡ„зҷҪиңЎж ‘
иӮ–зҺүиҺү
зҷҪиңЎж ‘иў«еҲЁжҺүд№ӢеүҚ пјҢ жҜҚдәІз«ҜжқҘзӣӣжңүж°ҙжһңзҡ„жүҳзӣҳж”ҫеңЁдәҶй«ҳеӨ§зҡ„ж ‘дёӢ пјҢ 然еҗҺжӢҝзқҖеҸ еҚ°еҘҪзҡ„зғ§зәё пјҢ еңЁж ‘еүҚжҷғдәҶдёүжҷғ пјҢ з”Ёжү“зҒ«жңәзӮ№зҮғ гҖӮ йӮЈж·Ўй»‘зҡ„зҒ°зғ¬з«ӢеҲ»еғҸиҪ»зӣҲзҡ„зҫҪжҜӣжӮ¬жө®еҚҠз©ә пјҢ дҪҷжё©ж•Је°ҪвҖҰвҖҰ
йҷўеӯҗйҮҢзҡ„еӣӣжЈөзҷҪиңЎж ‘е·Із»ҸеҸӮеӨ© пјҢ ж’‘ејҖдәҶжө“жө“зҡ„ж ‘иҚ« гҖӮ е®ғ们жҳҜзҲ¶дәІеҚҒеҮ е№ҙеүҚж ҪдёӢзҡ„ пјҢ дёҖиө·ж ҪдёӢзҡ„иҝҳжңүжқ‘иҘҝеӨҙйӮЈзүҮи‘ұйғҒзҡ„зҷҪиңЎж ‘жһ— гҖӮ
зҷҪиңЎж ‘жҳ“жҙ»жҳ“й•ҝ пјҢ дёҚз”Ёиҙ№е·ҘеӨ«еҺ»ж–ҷзҗҶ гҖӮ зҲ¶дәІиҖҒдәҶ пјҢ е’Ңеңҹең°жү“дәҶеӨҡеҚҠиҫҲеӯҗзҡ„дәӨйҒ“ пјҢ е’Ңеә„зЁјиҖій¬“еҺ®зЈЁдәҶеӣӣеҚҒеӨҡе№ҙ гҖӮ еңҹең°иҝҳжҳҜеҺҹжқҘйӮЈж ·е№ҙиҪ»еҜҢи¶і пјҢ иҖҢзҲ¶дәІеҚҙж„ҲеҠ жӯҘеұҘи№’и·ҡ гҖӮ з”°ең°дёҖж—Ұй—ІдёӢжқҘе°ұдјҡиў«йҮҺиҚүиҰҶзӣ– пјҢ жҜҚдәІиҜҙж ҪдёҠж ‘еҗ§ пјҢ еҜ№дәҺж Ҫд»Җд№Ҳж ‘ пјҢ 他们еӨңйҮҢеңЁзӮ•еӨҙдёҠеҸҜжҳҜи®ӨзңҹеҒҡиҝҮжҺўи®Ёзҡ„ гҖӮ жңҖеҗҺзҲ¶дәІе’ҢжҜҚдәІиҫҫжҲҗе…ұиҜҶ пјҢ е°ұж ҪзҷҪиңЎж ‘ гҖӮ иҜҙе№Іе°ұе№І пјҢ зҲ¶дәІжүҳжңӢеҸӢд№°жқҘзҷҪиңЎж ‘иӢ—е’Ңж ‘з§Қ пјҢ ж ҪдәҶдёҖз•ҰеҸҲ秧дәҶдёҖз•Ұ пјҢ дҪҷдёӢзҡ„еӣӣжЈөе°Ҹж ‘иӢ—е°ұж ҪеҲ°дәҶиҮӘ家йҷўиҗҪйҮҢ гҖӮ еңЁеҚ—еўҷж №е„ҝдёӢ пјҢ иҝҷеӣӣдёӘдҝҠдҝҸзҡ„вҖңе°Ҹ姑еЁҳвҖқејҖе§ӢжүҺдёӢж №зі» пјҢ з»ҪеҮәж–°з»ҝ пјҢ иһҚе…ҘдәҶиҝҷдёӘе№ІеҮҖзҫҺдёҪзҡ„еәӯйҷўпјҢ е’Ңе…¶д»–зҡ„ж ‘жңЁиҝһжһқеҗҢж°”ең°з”ҹй•ҝиө·жқҘ гҖӮ
д»»дҪ•дёҖз§Қж ‘жңЁ пјҢ еңЁжңҖеҲқзҡ„еҮ е№ҙйҮҢйғҪжҳҜйңҖиҰҒз”Ёеҝғдҝ®еүӘж–ҷзҗҶзҡ„ пјҢ зҷҪиңЎж ‘д№ҹдёҚдҫӢеӨ– гҖӮ ж ‘е’ҢдәәдёҖж · пјҢ ж—©жңҹзҡ„з®ЎзҗҶиҮіе…ійҮҚиҰҒ гҖӮ йӮЈж—¶зҡ„зҲ¶дәІжҜҸеӨ©ж—©дёҠиө·жқҘзҡ„第дёҖ件дәӢе°ұжҳҜеӣҙзқҖйҷўеӯҗйҮҢзҡ„йӮЈеӣӣжЈөзҷҪиңЎж ‘ пјҢ иҪ¬дёҠдёӨеңҲ гҖӮ зңӢзңӢе®ғ们йңҖдёҚйңҖиҰҒдҝ®еүӘ пјҢ йңҖдёҚйңҖиҰҒжөҮж°ҙ пјҢ йңҖдёҚйңҖиҰҒеҶҚж’’дәӣиӮҘж–ҷ гҖӮ еҰӮжһңеҸ‘зҺ°жңүеӨҡдҪҷзҡ„жһқдё« пјҢ д»–дјҡеҺ»еҒҸжҲҝжӢҝжқҘеүӘеҲҖжҜ«дёҚзҠ№иұ«ең°вҖңе’”еҡ“вҖқдёҖеЈ°еүӘжҺү пјҢ йӮЈвҖңе’”еҡ“вҖқеЈ°йҮҢжҖ»жңүдёҖдёқд»ӨдәәдёҚжҳ“еҜҹи§үзҡ„еҫ—ж„Ҹ гҖӮ д»–д№ҹдјҡйҡ”дёүеІ”дә”ең°жҸҗдёҖеӨ§жЎ¶жі”ж°ҙвҖңе“—вҖқең°зҒҢиҝӣзҷҪиңЎж ‘зҡ„ж №йғЁ пјҢ е®ғ们зҡ„ж №зі»е°ұдјҡиҙӘе©Әең°еҗ®еҗёзқҖ пјҢ ж°ҙзһ¬й—ҙиў«еҗёе…ү пјҢ еӣӣж•ЈејҖеҺ» пјҢ иҝҷеҗёеҠӣиҝҳзңҹдёҚдәҡдәҺе©ҙе„ҝеҗғеҘ¶зҡ„иӣ®еҠІе„ҝ гҖӮ иҝҷж ·ж ‘ж №и¶ҠжүҺи¶Ҡж·ұ пјҢ жһқеҸ¶и¶ҠжқҘи¶Ҡдё°иҢӮ гҖӮ
зҷҪиңЎж ‘ејҖе§Ӣзҡ„дёүдә”е№ҙжңүзқҖе©ҙе„ҝиҲ¬еЁҮе«©зҡ„зҡ®иӮӨпјҡж·Ўйқ’зҡ„иүІжіҪ пјҢ и–„еҰӮиқүзҝјзҡ„ж ‘зҡ®еҢ…иЈ№зқҖйӘЁиҙЁзҡ„е№І гҖӮ еҘ№зҡ„зӘҲзӘ•д№ҹжҳҜеӨ©з”ҹзҡ„ пјҢ еҘ№д»ҺжқҘйғҪжҳҜйӮЈд№Ҳзӣҙ пјҢ йӮЈд№Ҳжё…з§Җ пјҢ дҝ®й•ҝзҡ„ж ‘е№І пјҢ е…үжәңжәңзҡ„ж ‘иә« пјҢ йҖҸзқҖж·Ўж·Ўзҡ„з»ҝ пјҢ еғҸдёҖдёӘдёӘз§Җж°”зҡ„е°Ҹ姑еЁҳ гҖӮ еҘ№д»¬еҫҲе°‘жңүж—ҒйҖёж–ңеҮәзҡ„жһқжқЎ пјҢ еҚідҪҝеҒ¶е°”жңүи°ғзҡ®зҡ„жһқеӯҗжҺўе°ҶеҮәжқҘ пјҢ еҸӘиҰҒиҪ»иҪ»еүӘжҺү пјҢ еҘ№дјҡиҝ…йҖҹж„ҲеҗҲ пјҢ дёҚз•ҷиӣӣдёқ马иҝ№ пјҢ з»қдёҚдјҡеғҸзҷҪжқЁж ‘дёҖж ·з•ҷдёӢзЎ•еӨ§йҶ’зӣ®зҡ„з–Өз—• гҖӮ е°ҸзҷҪиңЎж ‘й•ҝеҫ—зү№еҲ«еҝ« пјҢ жңүдёҖз§ҚеҲқз”ҹзүӣзҠҠзҡ„еҠІеӨҙе„ҝ пјҢ дёҚеҮ е№ҙе°ұиө¶иҝҮдәҶйҷўйҮҢе…ҲеүҚж ҪдёӢзҡ„жһЈж ‘ пјҢ иғңиҝҮдәҶй•ҝе®ғдёӨе№ҙзҡ„еұұжҘӮ пјҢ д№ҹи¶…иҝҮдәҶж—©е°ұз»“жһңзҡ„жҹҝеӯҗж ‘ гҖӮ
е°ұжҳҜиҝҷж ·зҡ„вҖңе°Ҹ家碧зҺүвҖқ пјҢ еңЁзҲ¶дәІзҡ„е‘өжҠӨе’ҢжңҹжңӣйҮҢз”ҹй•ҝгҖҒиң•еҸҳеҫ—ж—ҘзӣҠеқҡйҹ§е’ҢзІ—еЈ® гҖӮ
е…ҲжҳҜзҷҪиңЎж ‘зҡ„ж ‘зҡ®дёҚзҹҘдҪ•ж—¶еҸҳеҫ—ж·ұжІүгҖҒжө“йҮҚиө·жқҘ пјҢ жҺҘзқҖ笔зӣҙзҡ„ж ‘е№ІдёҠзјҖж»ЎдәҶеқҮеҢҖжңүиҮҙзҡ„ж–‘зә№ гҖӮ ж ‘еҶ д№ҹжёҗжёҗж’‘еҮәдәҶдјһзҡ„жЁЎж ·дёҺиҚ«еҮү пјҢ з»ҝеҰӮзҝЎзҝ зҡ„еҸ¶еӯҗж—ҘзӣҠз№ҒеҜҶгҖҒжңүи¶Јиө·жқҘ пјҢ еёёеңЁйЈҺйҮҢж¬ўе–ңең°ж‘ҮжқҘж‘ҶеҺ» гҖӮ еҲқеӨҸж—¶иҠӮ пјҢ жһқеҸ¶й—ҙжӮ„жӮ„зјҖж»ЎдәҶиҪ»е·§зҡ„з§Қеӯҗ пјҢ йӮЈз§Қеӯҗжҷ¶иҺ№жүҒй•ҝ пјҢ дёҖдёІдёҖдёІзҡ„ пјҢ еғҸз»ҝиүІзҡ„жөҒиӢҸ пјҢ йЈҺиҝҮеӨ„ пјҢ еёёеҸ‘еҮәвҖңеҲ·еҲ·вҖқзҡ„е“ҚеЈ° пјҢ еҰӮеӮ¬зң зҡ„д№җжӣІ пјҢ еёҰзқҖжҜҚжҖ§зҡ„жё©жҹ” гҖӮ жҲ‘е–ңж¬ўе’ҢзҲ¶дәІеңЁзҷҪиңЎж ‘жһ—йҮҢеҫҳеҫҠгҖҒеҖҫеҗ¬ пјҢ ж„ҹи§үеҘ№д»¬зҡ„иә«дёҠжңүдёҖз§ҚжІ»ж„Ҳзі»зҡ„зҘһеҠӣ гҖӮ
йҡҸзқҖеІҒжңҲзҡ„жөҒиҪ¬ пјҢ иҝҷдәӣзҷҪиңЎж ‘з”ұзҲ¶дәІзҡ„еёҢжңӣд№ҹеҸҳжҲҗдәҶ全家дәәзҡ„еёҢжңӣ гҖӮ жҲ‘жӣҫж— ж•°ж¬ЎзңӢеҲ°зҲ¶дәІжҠҡж‘ёиҝҮйӮЈдәӣж ‘ пјҢ йӮЈдәӣж ‘зҡ„ж–‘зә№ пјҢ йӮЈж–‘зә№йҮҢеҚҮи…ҫиө·жқҘзҡ„еёҢеҶҖ гҖӮ зҲ¶дәІйӮЈз”ҹж»ЎиҖҒиҢ§зҡ„жүӢе’ҢзҷҪиңЎж ‘зҡ„ж–‘зә№жңүдёҖз§ҚеӨ©з„¶зҡ„й»ҳеҘ‘ж„ҹ пјҢ ж—¶й—ҙд№…дәҶ пјҢ дҪ дјҡзңӢдёҚжё…е“ӘжҳҜж ‘ пјҢ е“ӘжҳҜжүӢ пјҢ жҲ–иҖ…жҳҜж ‘жҲҗдәҶжүӢ пјҢ жүӢжҲҗдәҶж ‘ гҖӮ 他们еҪјжӯӨжё©жҡ–зқҖдёҖиө·й•ҝеӨ§гҖҒеҸҳиҖҒ гҖӮ ж— ж•°дёӘй»ҺжҳҺе’Ңй»„жҳҸ пјҢ зҲ¶дәІжҖ»еңЁжҜҚдәІзҡ„её®еҠ©е’ҢжҢҮзӮ№дёӢ пјҢ дҝ®еүӘе®ғ们 пјҢ д»ҘдҪҝе®ғ们жӣҙеҠ иҢҒеЈ®гҖҒжҢәжӢ” гҖӮ йҡҸзқҖж—¶й—ҙзҡ„жөҒйҖқ пјҢ дәәзҡ„еқҡйҹ§е’Ңж ‘зҡ„жҢәжӢ”жёҗжёҗиһҚеҗҲеңЁдёҖиө· гҖӮ
еҚҒе№ҙж ‘жңЁ гҖӮ жӨҚзү©зҡ„з”ҹй•ҝйҖҹеәҰжҳҜжғҠдәәзҡ„ гҖӮ йҷўеӯҗйҮҢзҡ„еӣӣжЈөзҷҪиңЎж ‘已然йҒ®дҪҸдәҶеӨ§еҚҠдёӘеӨ©з©ә пјҢ ж ‘зҡ„еҝғжҖқи—ҸдёҚдҪҸдәҶ пјҢ жңүдёҖз§ҚвҖңеҘіеӨ§дёҚдёӯз•ҷвҖқзҡ„и¶ӢеҠҝ пјҢ дҪҶжңҖе…Ҳз•ҷдёҚдҪҸзҡ„иҝҳжҳҜзҲ¶дәІ гҖӮ
зҷҪиңЎж ‘ж ҪдёӢзҡ„第д№қдёӘе№ҙеӨҙ пјҢ жҳҘеҜ’ж–ҷеіӯ пјҢ ж ‘жңЁзҡ„жһқеӯҗеңЁйҳҙйЈҺйҮҢж’•жүҜзқҖ пјҢ е°Ҹе«©иҠҪеҒҡзқҖжҳҘеӨ©зҡ„з»ҝжўҰ гҖӮ зҲ¶дәІеңЁеЈ®еӨ§зҡ„зҷҪиңЎжһ—ең°еӨҙиЎҢиө°гҖҒй©»и¶ігҖҒеҮқжңӣдәҶи®ёд№… пјҢ д»ҝдҪӣдёҖеңәж·ұжғ…зҡ„е‘ҠеҲ« гҖӮ й«ҳеӨ§жҢәжӢ”зҡ„зҷҪиңЎж ‘й»ҳй»ҳж— иҜӯ пјҢ жһқжқҲй—ҙдјјжңүж— ж•°еҸҢзңјзқӣеңЁеӣһжңӣзқҖзҲ¶дәІ гҖӮ зҲ¶дәІжңүдәӣз–Іжғ«ең°еҜ№жҲ‘иҜҙпјҡвҖңжҲ‘зҙҜдәҶ пјҢ жғіеӣһ家жӯҮдёҖжӯҮ гҖӮ вҖқжҲ‘зңӢеҲ°д»–зҡ„зңјйҮҢйҖҸеҮәд»Өдәәз–јжғңзҡ„з–ІеҖҰ гҖӮ жҲ‘йҷӘзқҖд»–иө°еӣһ家 пјҢ и·ҜдёҠд»–иҜӯж°”е№ізј“ең°иҜҙпјҡвҖңд»ҘеҗҺ пјҢ иҝҷдәӣж ‘з”ұдҪ жӣҝжҲ‘зңӢжҠӨзқҖеҗ§ гҖӮ вҖқ
йӮЈдәӣе№ІеҮҖгҖҒеқҡжҢәгҖҒе…·жңүжҜҚжҖ§е…үиҫүзҡ„зҷҪиңЎж ‘зңҹзҡ„е°ұиҝҷж ·иў«зҲ¶дәІжҠӣејғдәҶ гҖӮ
зҲ¶дәІиө°еҗҺ пјҢ жҜҚдәІжҖ»д»ҘдёәжҳҜиҝҷдәӣж ‘иҝҮж—©ең°еҗёиө°дәҶзҲ¶дәІзҡ„зІҫйӯӮ пјҢ еӨ©еӨ©еҝөеҝөеҸЁеҸЁ пјҢ еӨ©еӨ©еҝөеҝөеҸЁеҸЁпјҡйҷўеӯҗйҮҢж ‘еӨ§жӢӣйЈҺ пјҢ йҷўеӯҗйҮҢж ‘еӨ§жӢӣйЈҺе•ҠвҖҰвҖҰ
зҷҪиңЎж ‘еҲ°еә•иў«еҲЁжҺүдәҶ гҖӮ еҲЁдёӢд№ӢеүҚжҜҚдәІжӢҝжқҘзғ§зәё пјҢ йӮЈдёӘе№ҙиҪ»зҡ„еҲЁж ‘е·ҘдәәзңӢеҲ°еҜ№жҜҚдәІиҜҙпјҡвҖңдёҚз”Ё пјҢ дёҚз”Ё пјҢ ж ‘иҝҳжІЎеҲ°жҲҗзІҫзҡ„е№ҙйҫ„ гҖӮ вҖқдҪҶжҜҚдәІеҲ°еә•иҝҳжҳҜж‘ҶдёҠдҫӣе“Ғзғ§дәҶй»„зәё пјҢ еғҸйҖҒеҲ«зҲ¶дәІдёҖж ·иҷ”иҜҡгҖҒжӮІжҖҶ гҖӮ
йӮЈдёӘе№ҙиҪ»зҡ„еҲЁж ‘е·Ҙи„ұдәҶдёҠиЎЈ пјҢ е…үзқҖи„ҠиғҢ пјҢ з”Ёй“Ғй”ЁеӣҙзқҖж ‘зҡ„ж №йғЁ пјҢ еҫҲеҝ«е°ұеҲЁеҮәдәҶдёҖдёӘеңҶеңҶзҡ„еӨ§еңҹеў© пјҢ йӮЈеңҹеў©з»“з»“е®һе®һең°еҢ…иЈ№зқҖеәһеӨ§з№ҒжқӮзҡ„ж №зі» гҖӮ ж ‘иў«иҪ°з„¶жӢҪеҲ°еҗҺ пјҢ жҲ‘们зҡ„еҝғйҮҢдјјд№Һд№ҹжңүдёҖеә§ж— еҪўзҡ„еұұеҖ’еқҚ пјҢ йҡҸд№Ӣ пјҢ еңҹеў©иў«иҚүз»ідә”иҠұеӨ§з»‘иө·жқҘ гҖӮ еҗҠиҪҰй•ҝй•ҝзҡ„жүӢиҮӮд»Һй«ҳй«ҳзҡ„йҷўеўҷеӨ–дјёиҝӣжқҘ пјҢ зҷҪиңЎж ‘иў«жҷғжҷғжӮ жӮ ең°еҸјеҗ‘еҚҠз©ә пјҢ еҘ№зҡ„иә«еӯҗй«ҳеӨ§еқҡжҢә пјҢ ж ‘еҶ йқ’зҝ иҢӮзӣӣ пјҢ еғҸжһҒдәҶе–қйҶүдәҶй…’йЈҳеҗ‘еӨ©еӣҪзҡ„зҲ¶дәІ гҖӮ дҪҶж„ҝејӮең°д»–д№Ў пјҢ дёҚз®ЎжҳҜж ‘ пјҢ иҝҳжҳҜдәә пјҢ йғҪиҰҒжҙ»еҮәиҮӘе·ұзҡ„ж ·еӯҗ пјҢ жүҺзЁіж №зі» пјҢ еҠӘеҠӣз”ҹй•ҝ гҖӮ
дёүжҜӣжӣҫиҝҷж ·еҶҷйҒ“пјҡвҖңеҰӮжһңжңүжқҘз”ҹ пјҢ иҰҒеҒҡдёҖжЈөж ‘ пјҢ з«ҷжҲҗж°ёжҒ’ гҖӮ жІЎжңүжӮІж¬ўзҡ„е§ҝеҠҝ пјҢ дёҖеҚҠеңЁе°ҳеңҹйҮҢе®үиҜҰ пјҢ дёҖеҚҠеңЁйЈҺйҮҢйЈһжү¬пјӣдёҖеҚҠжҙ’иҗҪйҳҙеҮү пјҢ дёҖеҚҠжІҗжөҙйҳіе…үвҖҰвҖҰвҖқ
еҰӮд»Ҡ пјҢ ж•…д№Ўзҡ„и·Ҝиҫ№з«ҷж»ЎдәҶиҝҷж ·зҡ„зҷҪиңЎж ‘ пјҢ еҰӮз»ҝиүІзҡ„й•ҝеҹҺ пјҢ и‘ұиҢҸзҝ з»ҝ пјҢ дҝҠдҝҸжҢәжӢ” гҖӮ жҲ‘еқҡдҝЎе…¶дёӯе®ҡжңүзҲ¶дәІж Ҫеҹ№иҝҮзҡ„дёҖжЈөжҲ–еҮ жЈө пјҢ еҘ№д»¬ж·ұж·ұжүҺж №дәҺж•…д№Ўзҡ„еҺҡеңҹ пјҢ жү§зқҖең°еҗёе°ҳзәіеһў пјҢ еҗҗйңІз»ҝиүІзҡ„иҠ¬иҠі гҖӮ
гҖҗзҷҪиңЎж ‘|зҲ¶дәІж ҪдёӢзҡ„зҷҪиңЎж ‘гҖ‘дҪңиҖ…з®Җд»ӢпјҡиӮ–зҺүиҺү пјҢ йҳідҝЎеҺҝдәә пјҢ ж»Ёе·һеёӮдҪң家еҚҸдјҡдјҡе‘ҳ пјҢ е°ҸеӯҰиҜӯж–Үж•ҷеёҲ пјҢ е°ұиҒҢдәҺйҳідҝЎеҺҝ第дёҖе®һйӘҢеӯҰж Ў гҖӮиҙЈд»»зј–иҫ‘пјҡжқЁеӯҹеӯҗ
жҺЁиҚҗйҳ…иҜ»
- 科еӯҰжҺўзҙў|жҸӯз§ҳжҳҹйҷ…зү©з§Қиө·жәҗпјҡеӨҡдёӘиЎҢжҳҹеӯөеҢ–еҷЁз»„жҲҗвҖңз”ҹе‘Ҫд№Ӣж ‘вҖқ
- зғӯзӮ№|еӣ е°Ҹеӯ©зҺ©зҒ«еј•зҮғпјҢ407еІҒжўЁж ‘иў«зғ§з©әеҝғд»ҚиғҪз»“жһңпјҢйқ ж ‘зҡ®еҗёж”¶е…»еҲҶ
- 科жҠҖж—ҘжҠҘ|и·Ҝиҫ№ж ‘дёҠзҡ„иҝҷдәӣеҘҮжҖӘе°Ҹзү©д»¶йғҪжҳҜе®іиҷ«жқҖжүӢ
- ж Ҫеҹ№жҠҖжңҜ|еҸ‘еұ•жһ—дёӢж ‘дёӢй»‘жңЁиҖіж Ҫеҹ№жҠҖжңҜпјҢдҝғиҝӣжһ—дёҡз”ҹдә§еҸ‘еұ•пјҢеўһеҠ з»ҸжөҺ收е…Ҙ
- жқҺиғңеҚҺ|е„ҝеӯҗжӮЈз—…иҺ·еҫ—жҚҗж¬ҫ6дёҮе…ғ зҲ¶дәІжүӢеҶҷж„ҹи°ўдҝЎиҮҙи°ўеҘҪеҝғдәә
- еҰ–зҒ«еҺҶеҸІи§Ӯ|еҲҳйӮҰеҪ“дёҠзҡҮеёқд»ҘеҗҺпјҢжҳҜжҖҺд№ҲеҜ№еҫ…иҮӘе·ұзҡ„зҲ¶дәІзҡ„пјҹ
- зҺӢз’Ү|4еІҒзҡ„е°ҸйҮ‘дјҰпјҢиҝҳдёҚзҹҘйҒ“зҲ¶дәІе·Із»ҸзүәзүІвҖҰвҖҰ
- ж ‘иҺ“жҙҫдә§е“Ғжӣҙж–°жҚўд»Ј DIUSTOUз”өеӯҗе…ғеҷЁд»¶ж ‘иҺ“жҙҫ4жөӢиҜ„жқҘе•Ұ
- зҺүж ‘е·һ|зҺүж ‘вҖңеҢ—дә¬зҸӯвҖқиө°еҮәдёүеҗҚе·һй«ҳиҖғ第дёҖ
- зҲ¶дәІ|зҲёзҲёеҸ‘дәҶдёҖж®өи§Ҷйў‘еҲ°е„ҝеӯҗзҸӯзә§зҫӨпјҢзһ¬й—ҙзӮёй”…пјҢжғҠеҠЁиӯҰж–№пјҒ